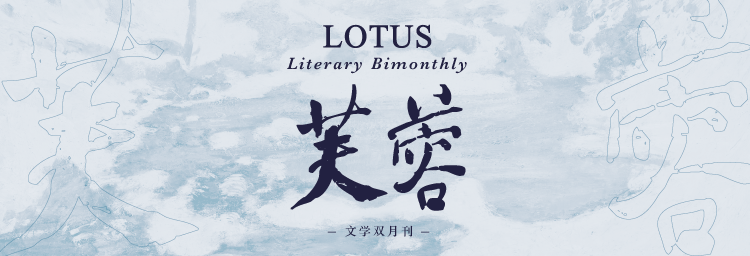

西郊陆家(中篇小说)
文/苏宁
1
“一次一块砖的钱就可以。”
“那你还值什么钱。”
“值很多砖钱。”
“你张口就谈砖。”
“我是谈钱。”
“一个三五百平方米的庭院不需要多少砖。两层一共二百平方米的房子也不需要多少材料。”
恍惚间,陆范又回忆起这个对话。自己坐在卡车的驾驶座上,弟弟站在路边。
妻子每次来探视,都会报告一下家里新近的变化。这两次来,主要报告了物品的添置。他要回家了。
“如果只是变老,那没意思,这样的老让人厌烦。”妻子说弟弟这两年衰老了很多。头发都白了。他写信问弟弟,弟弟的回复却简短到只有两行字。
弟弟帮家里买了一处新房子。自己出狱就能搬去新家。这让陆范睡不着。在狱中十二年,陆范改变了太多,回家住一个什么样的房子,过什么样的日子,出去做一件什么事谋生,是他心上每天都在过的事情。这是弟弟买的第二个房子。距市中心不过三四十分钟车程,一栋三层半的房子,差不多就是从前那个家的位置。
从前的果园,现在几乎是城中心地带了。这个房子,有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小院子,已经装修好。妻子告诉陆范,院子虽然小了很多,但就是爸妈、我们从前住的房子的位置。妻子还没有搬过去。她要等陆范出来一起过去住。一个完全的圆被剪开了豁口,搁谁心上,都摆不住,但在妻子、儿子心上,却摆了十二年了。
妻子现在住的一栋房子很小,普通的两居室,不到六十平方米,但却有一个不错的学区,为了孩子读书,这是二弟卖了自己房子再加上积蓄买下的。
自己进去时,儿子正读三年级。在城郊的村小,五年级开学转来市里,然后又是三年初中、三年高中,现在,儿子已经是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了。
二弟的儿子比陆范的儿子小一个年级,今年是大二了,学的气象学。姐姐的女儿和小姨一样上了师范。这三个孩子这么齐刷刷地一出来,陆范的心亮堂得自己都能照自己了。
陆范好像看到二十几年前的自己,和二弟站到一起,两个虎虎生风的后生。
当年自己入狱时还是一头黑发,只是十一二年光景,就没有一根黑发了。陆范出来这天,是妹妹和妻子来接的。二弟本来说了一起来,临出发的早上,却忽然说,有件事,不来了。这十几年,他心里一天也没放下这个比自己只大上一岁的哥哥。
前两天,给哥哥的车也买好了,一辆小轿车,不是货车。哥哥的手,离不开方向盘。
陆范从二十岁考下驾照开始,就是个跑长途的大货司机。此地向外发出的货有:布匹市场的布、码头乡镇上产出来外销的太阳能、紫薯桥的大米、两河一带酒厂里的酒,只要货到的地方,陆范都去送过货。
向北,陆范去过大兴安岭附近的城市,比如齐齐哈尔。有一年,他往那儿送过几车布,还送过一次棉花。
向西是新疆,乌鲁木齐、石河子这几个城市,每年七八月他都往那儿跑几趟,回来也不空车,瓜果梨桃装得满满的,怕路上耽搁久,果子会烂掉。他总是连夜跑,有时连个真正的副驾主家都舍不得再花钱找——跟着车的,有时只是个做样子的货主或货主亲属。二十多年以前,并不严查一辆货车是单驾还是双驾的问题,也没有安装GPS定位。
广州、珠海更是长年跑。货车司机陆范有不一般的沉稳和耐心。他以为他这一生除了没活时跟父亲种果树,就是做替人驾驶货车的零工了。
要出来前,二弟问过他,出来可有自己想法。
他说,我当然还是开车去。
关于狱中生活,陆范不太向家里说,也并不以为苦。真心话,以前天天开着车在路上,就是想趴下来好好睡一觉,但总是这趟到家了,另一趟车又要出了,循环无尽。
心里盼着休息,但更怕的,则是没有活干。
一没有活,家里揭锅就困难了,靠那几棵果树,只能换得吃上饭,要想一星期吃一次、两次肉,把各种开销打点清,还是要出去做这开车的零工。
在果园一带,能开好车,是一门大技术,比出去搬砖、和水泥,舒服自在多了。驾驶室里一坐,那是风不打头,雨不打脸,多少小伙子羡慕呢。
陆范家里往上三代,都是城边上的果农。最近这三四十年过来,一家人就那么守着这百十棵果树,一年到头,做着果农。每天干的都是请老天爷赏饭的事,要望天看收成。
在果树开花、坐果或果实成熟期的任何一个时期,赶上两场大风雨,就收不到东西了。若是花期,花被打落,花不可能一年再开出一次来,这就没有了结果的可能。果子结出来了,两场大雨一下,也会一切全完——没熟的青果打落了是再熟不起来,再回不到枝上。熟果若被打落了,一经雨水,没两天也就烂了一地。
陆范除了会种果树,开货车,其他事什么也不会——算来,会的也都不是什么特别的事,逢上年份不好,活少,体面地糊口都有问题。
当货车司机是一份零工,不可能每天都接到活。运送货物的出发、抵离时间由要货的和供货的决定,由不得自己。只要想挣这份钱,路上的时间就要全听他人安排。
好在力气是老天白给的,天天给来一份,今天用完了睡一觉又来。这份力气,完全可用它生活 、做事、养家,果园里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2
果园里有两条河,很小很细,终点都是淮河。两条河各有名字。一条河叫范河,一条河叫戴河。因为这条河而有两个村,一个范村,一个戴村,都紧贴着城西。从西边出城,下到县里乡里,都过这两个村。对于下边的乡里人,这是城里的地界了,而对城里,它又妥妥是个乡下。
河与村名皆源于此地范、戴两姓人居多。两村后期合并,名为双河。以前立过村碑,碑上写的是“双和”。此碑拆掉后,就地修了一个菜场,名双和菜场。
陆范上面有一个姐姐,二弟比自己小一岁。二弟下面还有两个妹妹。自己被爸爸起名为陆范,二弟被爸爸顺手起名为陆戴,当年市体校下到果园选体育特长生,看中了二弟是一个摔跤的好苗子,将二弟选进了体校。当了运动员的二弟,因此成了果园里的名少年。陆戴去学摔跤,成为一家人的荣耀。爸爸用瓜果梨桃换来的钱给陆戴交学费、营养费。
果园里的人家都无现钱可用,只能靠熟透的果子换,不拘年成好坏,换来的钱都要分成十二份用一年,用到明年的果子再结出来。
少年陆戴也打过几次比赛,后来在一场比赛里意外摔伤退役。在体校时,孩子们都是住校的。一个宿舍住八个人。当年的体校宿舍,每个宿舍里的孩子,喜欢按年庚大小排序,这些同宿舍的少年也就一年两年之差,基本区分在出生月份有前后,陆戴排到第七。
三十年前,果园开始拆迁。果园被加了围栏,变成收费的植物园。在这一带住过的人,提起当年的少年陆戴,大多不叫其陆戴,而呼为陆家那个二小子,陆家弟弟,或者陆二。有时也被人叫作陆七。这陆七不是在家里排序第七,而是在当年体校宿舍里的排序。陆二在体校读书几年,虽然打过一些比赛,但没有被进一步向上选拔。退役后被安置在郊区一个小学,做了一名人民体育老师。
教了几年体育,一届小学生还没带到尾,体校毕业的小七同学就辞职了。一是他所在的这个小学马上要和另两个小学合并,体育老师多出来,要转去教其他科目,教导处和他谈的科目是小学思想品德,类似中学政治那样的一门课程。二是学校要求小七同学这样出身的体育老师转职前要先完成进修提升,进修时间要保证一年以上,进修的学校可以自己找,也可以让学校联系。进修期间只发基本工资。
基本工资听着好听,实际上连进修期间自己的食宿费都不够,何况家里刚添了一张就要会自己吃饭的小嘴。小七的结婚对象是地道的城里姑娘,虽是一个普通的商场售卖员,但在果园的人看起来也是有正经工作的。
这姑娘的加入,对陆家有着鲜明的阶层提升的意义。果园的人,把一切能不和泥土沾到一起的事情,都视为神圣,是“正式工作”,做的是正经事,是国家给的。他们把国家给或者派定的工作视为“荣耀”,哪怕只是在纺织厂里做一个三班倒的纺织女工,那也是比在果园劳动光荣、高尚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劳动可以直接拿到现金工资——在果园里,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只有收获了果实,通过贩卖才可能见到现金。且变现程序复杂。直接卖是一道手续。大多数时候,要加上一道周转,比如,运果实去一些更远的、种粮食的镇上,先用果实换来粮食,再将粮食找地方卖出去,然后看到现钱。
这个过程消磨着人心和意志。一棵树要等它长大,然后再等它会开花,其间,它把一个人的一天、一年、一生都留在这样的状态里,你要去侍候和等待它们。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也不需要什么外在支持,却不是每个人都有耐心去过。
这一个平凡的商场服务员,母亲是纺织厂职工,父亲在车辆厂,地道的劳动之家。但因为来自果园人不同的社会层流,在陆家上下的人看来,这姑娘是高看了自己家才肯嫁入的。体育老师陆戴也一心想着去厚待这一个姑娘,觉得不能让她跟自己受苦。
3
陆戴没有和家里说转岗合并之事,和妻子也只是淡淡地一提。果园的男人,长大不是靠年龄增长,是靠各种坏天气和逼仄的生存空间督促。陆戴私下里和两个情况差不多的老师一商量,互相一拧劲,觉得还是从学校出来吧。不谈长远,就说这近在眼前的一两年全脱产进修,个人境况都挨不过去,哪一天不花钱?这钱是能靠风吹来,还是让大地自己长出来?答案在那儿:风吹不来,地上也长不出来。
三个人有一个共同情况,都才有了家小,又都没有任何外来的经济援助。
陆戴家里,自从他当了这个小学老师,以为他已经混得多么好了,还等着他援手呢。妻子家里,也更是伸不出援手。
当然,如果不是这需要进修转岗的“坎”拦在这儿,日子慢慢过,平平淡淡以体育老师的身份终老,也是一份踏实日子,比果园安稳很多倍的日子。而且,这小学思品老师当一辈子,真也是很好。
陆戴从教师队伍中走出这一年,刚过二十九岁,正处在三十岁的前站。
出来的第一站,陆戴开了一家体育运动用品商店。陆戴的店开张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父母在果园的房子,突然被通知拆迁。
父母无法接受住了两三代的房子被拆掉,也接受不了拆迁方提出的条件。耗了几个月之后,一左一右的人相继签了同意。父母之前也听说了果园里住户要拆迁,但没想到那么快。家里这几年收成一般,孩子又多,四处用钱,就没有来得及腾出钱把原来的房子加盖出一些面积。这一次拆迁折算的恰是住房面积而不是人口。
原来的房子只是简单的两层,但院子很大,因为几代人都住在果园,位置也是果园里一等一的肥地。
不拆是不可能了,但父母退而求其次地想凭这块好地势,能多得一些补偿。周围一些位置不那么好的人家、态度蛮一些的,结果都比较理想。还有些人家,是四处托了人帮说话、打招呼的。这是一对见了生人说话都难的老实人。父母让陆戴出面找人——祖宗三代里,就他一个在城里读过书,见过世面,父母遇了这么大的事,只有找有用的儿子。
按果园人的行事风格,凡是遇事,要遵从“家有长子,国有大臣”的理,但二老目光敏锐,直接略过了风光地、四处开着一辆大卡车的大儿子陆范,找了第二个儿子陆戴。
在父母那儿,这是个绝对的熟人社会,情义在哪儿,理在哪儿。陆戴想了几天,自己除了同学,宿舍的几个兄弟,也没其他朋友和这拆迁队有联系。而且,理在自己家这边,凭什么自己好好的房子说拆掉就给拆掉?父母亲日子过得好好的,穷是穷点,但凭什么要换一个地方去过?这一个月 ,拆迁办的人员,天天一上班,就来家里坐着,天黑也不走,让父母签字。最后的期限转眼就到了,但他们根本听不进父母的倾诉,只是不停地批评父母觉悟低,不支持城市发展建设。爸爸让陆戴回家,多少增加个照应。
这一天,陆戴回了家。临时的拆迁办公点就在进果园的路口。陆戴拐进去,恰好父亲也在那儿 ,一早被工作人员找过来谈心。一杯热茶也没喝到,只是又接受了一通教育,陆戴听得头疼。
第二天,陆戴再回家,又拐进了临时的拆迁办,昨天那一副面孔和理论又迎了过来。这一次,父亲不在。
墙上一溜是规划图,撕坏了赔也不值。陆戴手袖在背后,眯眼看了一会儿,看了又看,心里生气。一时气起,曾经的摔跤队少年,一双肉手推开去,三张办公桌哗啦啦倒得四脚朝天。又一通狂掀,半边简易房也揪歪了。看着房子在眼前歪了下去,陆戴息了怒,静下。自己倒了杯水。
昨天满腹城市发展理论的接待员吓跑了。不一小会儿,换了两张新脸进来,陆戴在气头上,根本不怕打架。上去就去抓一个人的衣服领子。另一个一看,也僵住了。一会儿,过来一个平事的,把陆戴让到另一个办公室,坐下,上了热茶。
陆戴说:“我没力气把昨天的话讲一遍了,我讲过了。”
曾经的体育老师陆戴人看着并不斯文,又因为长得高大,沉着眼睛,脸上、身上一看,就是有一把好力气的。让人看了有寒气。把昨天接待陆戴的那个肥胖女接待员招来,那女接待员瞟到陆戴气势森森地坐那儿,也自谦卑了一层,迅速、简短也客观地把事情的焦点说出来,昨天陆戴父亲的话,也帮重述了一遍。
“先喝茶。”对面的人看着是这里的头。
“我们这些干部,总是心里想着为群众着想,一着急就走偏。我向你道歉。这次拆迁,对远景规划和政策宣传太不够,太简单了,行事也粗暴,我们检讨。”
陆戴怕礼不怕兵。对方这么一虚心,自己也松弛下来,强将不打行礼人,做人有理也要给人下台阶。
陆戴长得壮硕,人支在那儿,根本不是父亲那一副到哪儿都唯唯诺诺、低人一等的气象。
“历来长得不像好人,这个长相看着就不讲理、不善良,是吧,让人想到是菜场里天天杀大牲口的。”这是陆戴的自嘲。确实,他长得又黑,根本不像前面几次来的那个矮弱的、老年的果农的儿子,像是赤手过来打拳击赛的。
脸上肉长得也横横的,没文明气,这是后来那个女接待员对陆戴容貌的描述。
实际上,平时街上所见的陆戴,高大帅气,温文尔雅,不像摔过跤的,行走坐立姿容挺拔,像一个经过严格的、标准化训练的好士兵,是果树园几十年也养不出来的好材料。
陆戴的拳头松下来。像忽然遇到了熟人一样,陆戴坐下来,端起了水杯。
能端对方递来的水杯,从心理上,陆戴已经在给对方解决问题的余地了。
但陆戴口里说的是:“我今天就是来打架的,我和你们讲不过理。我爸也穷。我是不怕出人命的。”陆戴从衣襟里拿出一把很小的包了羊皮鞘的小水果刀,放到桌上,“我本来也不想出人命,但气这份上,也没有其他办法。这刀,你们别怕,我是用它了断我自己的,我这个儿子不争气,让老的只有这一个小房子。”
“理解,理解,是我们太简单。您千万莫气,莫这么做、这么想。是我们宣传讲解不够,方案也不细。”
然后,领导自报姓名。又问陆戴名姓。两个人像在酒桌上相见一样,互报了名姓。叙事、叙情,一叙,拐弯的同学,拐弯的父老乡亲都叙出来了。
(节选自2023年第4期《芙蓉》中篇小说《西郊陆家》)

苏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江苏淮安。作品见于《十月》《人民文学》《钟山》等刊。著有《平民之城》《一座消失的村庄》《我住的城市》等。
来源:《芙蓉》
作者:苏宁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