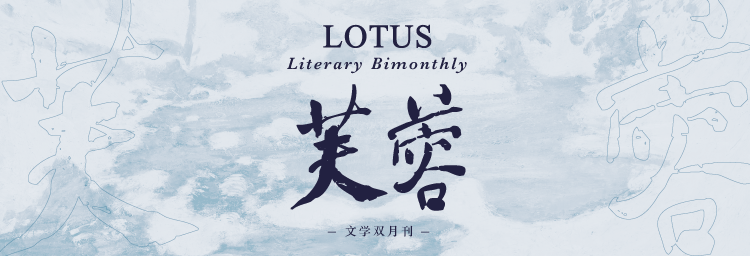
从清晨,直到深夜(中篇小说)
文/弋铧
电梯里,人比较多,比平常钱德新出门的时候要更拥挤些。他紧贴在一位男性的身后,眼光看到那人的后颈项,剃得有点冒青茬的头皮,略略分散着一些红色的小瘤,凹凹凸凸的,不知道是何种皮肤病。钱德新心生厌恶,低下头,挪动的幅度碰着后面的那位女士,女士非常提防地举起方方正正的公文包,护住自己胸部,又掌控尺寸,挪到私密处,铜墙铁壁般地严防死守,似乎钱德新会用背部躯体骚扰她。钱德新冷冷地哼哼鼻孔,有些气味趁机混浊地闯进他的鼻腔,似乎有男人用的古龙香水味、晨起的床气、早餐未消化完的反刍、隔夜的猫尿臊味,甚至还有垃圾的酸腐味,当然,女性用的某种强烈的海洋调香水味更浓郁些。这种气味让钱德新陡生出记忆里的片段来,他愣一愣,在大脑海马区搜索一番,还没有得出定论,一楼就到了。
从地面层出口处一出来,空气陡然清新。花草的淡淡香气扑面而来,洒水车刚清扫过马路,原本浅灰的路面洇出湿漉漉的水汽,演变成黑灰色的路面。也许是心理作用,钱德新明显感觉到路上的车流比往日少。顺着车流往远处看,道路尽头和灰白的天空相接,影影绰绰地有些黑绿的植被点缀其间,再往上眺,半轮疏月羞答答地挂着,和那轮明亮的红日比肩,欲说还休地将要退出舞台。
钱德新犹豫一下,随着人流,拾级上了人行天桥。
钱德新很少上这架天桥。晚上出去跑步,偶尔会从天桥穿过,往对面公园里跑。夜里的天桥很漂亮,横跨桥体,桥栏两边点缀着五颜六色的彩灯,那些有规律明明灭灭的光芒,吸引过往行人的眼球。桥体的建造风格,有点北欧式设计感,又带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潮流,还有些后现代的科幻色彩,算是一座不错的景观天桥。
晨起八点不到的日光,已经开始刺目。钱德新留意到,桥上虽明显打扫过,但也留下一些洗濯不净的污秽,有脏水的痕迹,也有夜里狂欢者酒醉后呕吐的残渍,还有刚刚过往的行人随手丢弃抑或不小心丢失的小物件。有只挂着蓝色门禁卡的钥匙环,有包已拆封的面巾纸,还有半杯应该是不慎滑落于掌心的豆浆,幸好封装的口子没有完全撕开,稀稀拉拉的液体只流出少许。桥上的行人脚步匆匆,没人对那串钥匙环和面巾纸有任何兴趣,它们被来往的行人踢踏,不断地变换位置。
只有那大半杯豆浆,还在原地坚挺地躺着,岿然不动坚守自己的位置。是等待主人过来拾取,还是等待有心人把它捡拾到垃圾箱内?也或者,只能守到清洁工过来,把它厌弃地归入那可回收垃圾桶内腌臜的黑色塑料袋中?
茫茫穿行的人流里,靠近另一边阶梯的地方,端坐着一个看不出年龄的乞丐。像大多数乞丐一般,他的面色是接近腌肉似的黄,在酱油打底,食盐防腐,最终经过太阳的曝晒后,呈现的那种油黄,却并不显脏相。他的头发稀疏,却是黑糙糙的,在脑后松松地绾成个髻。着一件看不清楚底色的灰或者白的衫褂子,盘腿坐在人行天桥的水泥地面上。正前方,摆放一张毛笔写就的告示,旁边有个打印好的二维码。放置在告示板上的,倒是互联网没有流行时乞丐们通用的讨钱钵,里面密密地塞满纸钞,一元的,十元的,还有几枚硬币,大约是为了不让纸币飞扬用来而做镇纸用的,定定地压在讨钱钵里。
钱德新停下脚步。刚出家门的时候,他摸到西装内袋里有枚硬币。这枚硬币有着悠久的历史,经过几次干洗都还完好无损地躺在内袋里,显示着老商家,那户城中村洗衣店店主的诚实和厚道,或许只是不屑?这年头,谁还会对一枚一元硬币有拿去占为己有的闲心?
钱德新把那枚硬币掏出,摸索一番,旋即丢到乞丐的讨钱钵里。硬币丢得非常准,他用眼角扫到那枚硬币弹了弹,然后和它的新伙伴一起,稳稳当当地窝在钵内。乞丐闷声说句:“谢谢您了,恭贺您好人好报,长命百岁!”
钱德新逐级而下阶梯,心里突然涌上一种兴奋,他感觉今天应该有些好运,至少,能够转运!他的脚步轻快起来,随着早起赶路的人流,往前涌去。
朝地铁站方向,行人密密麻麻。行道边的花花草草,随着人流的震动,也摇曳生姿,粉的、蓝的、黄的,各式叫不出名目的小花,还有树上开枝散叶破苞而出的花朵,也是乱哄哄的颜色,繁杂得叫人眼花缭乱,热闹得让眼眶都盛放不下。钱德新暗暗讥讽市政的审美。他一向喜欢单一色调的堆砌,大片大片的明黄银杏,或者一丛一丛的绯红枫树。他信奉简约美才是高级的。
走在路边,看满目充溢着的热闹,他愤愤地朝脚边的一坨赭褐色凋谢了的枯树丛踢了一脚。
那物竟然跳动起来,而且还带出一声凄厉的叫唤。随着那物的起伏,钱德新定睛看个明白,原来是一条跛足的黄狗,看它落魄的模样,肯定是只被遗弃的狗或者流浪狗。它的两眼有些不一样,左边的那只是黑色的眼圈,右边的那只,在黑色圆圈里夹杂一撮白毛。它的眼神朝钱德新小心地瞄过来,露着胆怯、谨慎、恐惧却又可怜的表情。
钱德新不喜欢宠物。儿子一直想买只宠物在家豢养,缠过他许久,妻子也跟着儿子说过两次,但钱德新不改初衷,坚决不想在自家屋里留一个畜生。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有过看门狗,谁家的父母都是不会让狗进家门的,只院子是那畜生的领地,甭管凄风苦雨,那畜生有那畜生的活法。所以,钱德新住到城里后,无法理解那些养狗人的痴情,视若己出,还给穿衣着帽,有专门的口粮,和主人平起平坐,有的还爬到床上?!
他可不想让儿子成为畜生的牵绊,缚住自己本性为人的根本。好日子才过上几天,就上房揭瓦了?钱德新不会惯出孩子这些毛病来。
他和那跛足的流浪狗对视两秒,他慢慢地朝它逼近,它警觉地往后倒退。他终于停下,仔细地盯住它,终至叹口气,在无数过往行人的侧目下,他放弃它,饶过它。他径直走掉。
今天是政府倡导的绿色出行日。钱德新原来没在意过这个,自从有车后,他几乎从不步行,或者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他压根没想过要做个有车却不开的人,他已经习惯了开车的日子,上班,休假出游,去商场超市买物品,甚至和羽毛球队的队友出去练球,他几乎没有过不开车的日子。没有车,他就像丢魂一般,不知道自己的双脚还能用来坐公车或搭地铁。没有车,他只感觉寸步难行。
这也不知是第几个绿色出行日了。自从市政府倡导这个日子以来,钱德新听同事朋友都说起过积极响应,而且他们也都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脸面上有着些许得意,似乎现在吃惯荤食的富人们,尝试某些野菜的苦腥,自得其乐得像下凡的仙者。但也就仅此一天,明朝会继续开着自己的座驾,加入浩浩荡荡的大肠包小肠的城市蠕动中,朝着城市的各个场所行进,一路排泄废气,制造噪声。钱德新多少有点看不上这种“作”,一时的朝拜,不代表一世的虔诚,他厌倦这些装模作样的套路,获得心理安慰的告解。
他的肚子咕咕叫唤两声。钱德新有些不好意思,路上的行人匆匆与他擦肩而过,并没有谁聆听到他的饥饿。他抬腕看下手表,多年养成的生物钟如此准时。往常这个时间段,他已经坐在家里的餐桌前,满心欢喜地享用妻子做好的早餐。
妻子自打怀孕后,便离职赋闲在家。他的经济状况一向不错,在公司里一直有上升的空间。那会儿他们俩正处于爱情的甜蜜阶段,刚结婚,组成美满的小家庭,对前途充满丰富而具体的向往。他希望妻子好好守家,诞下两个子女,一家四口能其乐融融地生活在这座陌生的大城市。妻子孕吐厉害,再也不想坚守“女人一定不能没有工作”的信条,打道回府,开始认真孕育孩子。
妻子的早餐做得极为丰盛,每周七天,从不重样,甚至半个月里,也没见她重复过菜品。特别是儿子开始吃主食后,妻子扮演母亲这个角色,已经得心应手,当初抚育儿子的束手无策力不从心,早变成现在的游刃有余驾轻就熟。
钱德新看到档口那个热火朝天的早点摊,许多搭乘地铁的上班族都在那里用手机支付买单,然后拿过老板递过来的一只只饱满的装着早点的塑料袋匆匆离开。他靠近,仔细研究档口贴出的早餐菜单。
他要了两只镇店的肉包,又要两只烧卖,长得有些圆滚滚的年轻老板娘麻利地把他要的东西分别放进两个塑料袋里,他刚想扫码付钱时,老板娘问:“不要点喝的吗?”他愣愣,才发现一只大玻璃柜里,摆满了名目繁多色彩纷乱的各式牛奶、奶茶和其他饮品。老板娘一边应付其他顾客,一边推荐:“我们家的豆奶是才出锅的,要不来一杯?”钱德新立马应下来,接受老板娘的推荐,拿过那大杯的热豆奶。
他从拥挤的早餐人群里夺路出来,模仿那些人的样式,站在马路牙子边,生疏地咬着包子,生疏地喝着豆奶。包子皮薄馅足,果真是镇店之品,豆奶有股怪异的味道,既不像豆浆,也不似牛奶,不知是怎样融合而成这样一种饮料。但是温热有加,喝进胃里,有种暖烘烘的舒心的感受,带出来的是经历过一晚空腹后的满足。
他朝早餐档口的那对夫妻看过去。两个人都穿背心式围裙,明黄间鲜红的色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番茄炒鸡蛋配色,亮堂而不易显现脏污,还带点富足的欢快。他们的人同样也是欢快的、雀跃的,带动他们的脸部表情,眉飞色舞,八面玲珑地招待着每位顾客,决不怠慢每一位顾客的要求。那背后升腾着热气的蒸笼,宣告他们一早的忙碌和辛苦。是几点就起来开始和面,调馅,烧锅,磨浆?他们有几个傍在膝边的孩子?每一天操作完后的计算利润,应该是洋溢着这一天苦尽甘来的欢欣。
他又咬一口烧卖,这是素馅的,能品出里面夹杂的料有青豆、香菇和红薯粉条。他喜欢吃带有红薯粉条的馅料,他的老家,包饺子和包子,都会搁红薯粉条,切得细细小小,如果和大肉鸡蛋碎调在一道,那便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了。钱德新有些想念自己的母亲。母亲在五年前过世,父亲是七年前走的,老家现在是没必要回去了,回去前没人盼着,离开后也没人想着。兄弟都有自己的家庭,早立门户,他再回乡,倒像是走亲戚,所以那个老家,那个户口上写着的祖籍和出生地,离他是越来越远了,远得让他觉得虚幻和缥缈,海市蜃楼般的存在。他当年发疯般地要离开那里,绝无可能会想着日后回去呢。钱德新思索一下,觉得根基这件事情太过哲学,只是存在,却并不合理。他摇摇脑袋,摆脱对故乡的那缕温情,仰头又喝下一口豆奶。这时,他看到那条跛足的黄狗蹒跚过来,眼带乞求怯怯地望着他。他想想,把剩下的那只肉包和最后一点豆奶残液,轻轻地放置在那畜生的脚边。
钱德新掏出纸巾细致地擦净双手,把其余的垃圾扔进街边的分类桶中,随着人流,向地铁站里走去。
地铁人流比想象中多得多,从入站口就排着井然有序的长队,大家面无表情地前后挨挤,保持着可容忍的社交距离,慢慢地挪移前行。上扶手电梯时,也还是排着整齐的队伍,全靠右侧,只两三个碎步小跑的人,从左侧蹿上去。钱德新思考那些跑过去的人,是想提前做什么呢?买地铁单程票?买地铁口商铺的速食点心做早餐,或者是去公厕出早恭?他到达检测口,送公文包进扫描机,拿公文包,再扫地铁卡,地铁口的安全闸开启,钱德新闪身进去。
队伍仍旧有条不紊,排在即将到达的地铁的各个入口处。钱德新目测一下,可能这班地铁自己挤不上去,抬腕看看手表,离上班时间还绰绰有余,他心情放松下来,观察着每天挤地铁上下班的人群。
多是年轻人,二三十岁居多,也有三四十岁的,和钱德新年纪相仿。这条线开往CBD,沿途很多大公司,往前四五站之后,就是中心地段,写字楼,大机构大办事处,乘客会陆续下车,前往自己的薪俸发放地,满满当当地干完八个甚至还要更多的工时。对面的另一条线,等车的乘客明显稀少,毕竟在这个时间点,从商业中心赶赴郊区居住或务工,好像真说不过去。钱德新定定眼神,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对门的女邻居。
她穿一件浅灰色长风衣,手里拎一个名牌手提袋,脚上是双半高跟漆皮鞋。那边因为候车的乘客少,越发显得她夺目。她的身姿很挺拔,从钱德新这边看,她似乎在站立的时候,尤其强调自己的姿态,整个身形都透出一种傲慢和居高临下,她精干的短发微微地往外翻翘,透出职场“白骨精”的果敢和强势来。而且,在这种时刻,在早晨或者说在室内,她不可思议地戴着一副遮蔽半张脸的太阳镜。
钱德新认真地研究女邻居。
他和她不算熟悉。搬过来八年,他和她讲话几乎没超过五句。印象中,女邻居很喜欢笑,爱主动打招呼。他记得八年前对门刚搬过来入住时,女邻居敲开他的门,非常自来熟地请他过去帮忙安装她刚给儿子买的一套玩具无人机。他当时不是特别乐意,但妻子非常好客,自作主张地替他应承,推搡他过去帮忙。钱德新当时有点不满也有些不解,他不算乐于助人的,也不明白为什么对面的男主人不承担这种义务。他很认真地安装那套玩具,在那个调皮小子不停的催促下,把那套价格不菲的无人机递给女邻居。他当时的脸面不一定是冷酷的,但也绝不能说是热情。此后,他再次遇到女邻居,没有对她热情洋溢的态度给予礼尚往来的回馈,女邻居渐渐地只笑露八颗细密的白牙,作为主动打招呼的礼节性问候。
女邻居长得很漂亮,在她这种年纪,在她生下两个孩子的背景下,她的身材也维持得很好,像八年前见到时一样。
她还有个大点的闺女,今年好像入读一所私立高中,比他的儿子年龄稍大一些,钱德新的儿子刚上初三,正是紧锣密鼓争取考上重点高中的时节,妻子对此俨然已成专家,每日的话题全是儿子的中考事宜。
“对门的没达到分数线。”他当时听妻子淡淡地提起过,她的话音里有些许不屑。他不太在意这些事情,他一直认为现在的教育有点过激,他认为儿子就算考不上公立重点,也完全有别的途径接受不错的教育。但妻子对此颇有执念,每每与她提及此事,她就像头暴怒的公牛,竖起犄角,准备和他决战一轮。他丢盔弃甲,狼狈逃窜,躲进自己的世界里,那平和安宁的独处中。

弋铧,女,生于湖北武汉,祖籍浙江嘉兴,现居深圳,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当代》《中国作家》《花城》《天涯》等刊物,部分小说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杂志选载。出版有长篇小说《琥珀》《云彩下的天空》、中短篇小说集《千言万语》《铺喜床的女人》。获首届鲁彦周文学奖,首届广东省“大沥杯”小说奖,第七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第一届、第二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
来源:《芙蓉》
作者:弋铧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