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者的诗
——读汤锋诗集《亲如未来》
文/彭燕郊
罗丹的“思想者”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强烈的震慑,惊奇于思想的强力同时模糊地感到那里面必定有深远的启示,但到现在还没能参透它。随着岁月的推移,随着对于这高坐于地狱之门上方的思考着的巨人的不知多少次的顶礼膜拜,我逐渐体味到这被罗丹物化了的可视的人类高贵的精神活动的无比丰富内涵,思想者是用全部循环系统滚热的血液、全部绷得紧紧的神经系,全部在活跃地生又活跃地死去的往复中忙碌着的细胞、不停息地向大脑输送思想燃料的心脏的搏动在思考着,毛细孔的每一次呼吸,肌肉的每一次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起伏,都说明思想活动的尊严与高贵性质。艰难和愉悦,狂暴的激情之后是澄明的沉思,对于旧观念的粗暴冒犯之后是对新生幼苗的无比柔情。我相信,思考是在经历着兴奋与平静,迷茫与领悟的轮回与奇妙结合的极乐,我能明白为什么他要用那厚重的手掌支撑他那千斤重的铁锤一样的头,由于专注于内心,他的头是低垂着的,暂时还看不到他的眼睛,但我相信,一旦他抬起头来, 那里面必定会喷出电闪般的光焰。我能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地坐着,腰弯得那么深,我相信他是在准备一次跳跃,这种姿势最适合力的喷发,在他发现眼前出现真知的某一个部分,不论大小, 他都会猛兽般扑下去,抓住猎物,然后再回到座位上,继续思考。
我学写诗,欣幸能够在但丁、歌德、鲁迅、波特莱尔……诗人身上见到这种力,诗化了的耐想的力,《神曲》《浮士德》《野草》《恶之华》……成为我的《圣经》,我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诗人出现,有更多的这样的《圣经》供我学习,我深信这是可能的,我深信人类文明的长河不会断流,现代诗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现代诗人是以思考为第一选择的,思考成为第一冲动,正如抒情成为浪漫主义诗人的第一冲动,现代诗人在思考中获得理性的升华,从而获得自我灵魂约束的能力。现代诗人以思考为诗人性格特征,浪漫主义诗人则以情绪化的语言为性格特征,终于导致了不信任感,而现代诗人的启示性语言则以思考引发思考,他们深知,思考是诗人的天赋,诗人的本份,诗人的历史使命。诗人是时代的忠实儿子。
经过不算太短的十多年的徘徊,中国新诗终于走出“玩诗”的魔障,近年以来,连接着出现一些优秀作品,这必须归功于我们的能够清醒地拒绝以说谎来引诱人说谎的别有用心者的怂恿,冷静地,认真地,甘于默默无闻地把生命奉献给真诗,以自己的行动捍卫真诗的诗人们 , 这里就有汤锋,有他的诗集《亲如未来》。
一
中国新一代的诗人是历史哺育出来的,有实力的新一代诗人是中国新诗的主力,主体, 中国新诗希望之所在。因为他们没有离开过哺育他们的沃土,我们悲壮的历史。
诗人是要飞翔的,然而他难道可以在空虚中起飞?历史才是坚实的基地。
诗人汤锋曾经把自己比喻为一匹天马 :
一匹天马 , 尽管它曾经遭受过种种磨难和折腾
但它同样驮着善良者的沉重 , 驮着
地球上的惶惑和怨恨
以及长期在扭曲中存活的无辜者和不幸者
在它自己的世界中永恒地向前飞奔,向前飞奔 ……
——《隐秘的天马》
我们当然不可以认为这匹马是从遥远年代的浪漫主义世界中飞来的,遍身血污,历尽艰辛依然驮着诸世纪的不幸,“在它自己的世界中”飞奔着,而且是“永恒地”飞奔着。这是献身,是心甘情愿地飞奔向殉道的祭坛,在汤锋,诗人就应该是这样的。这使我们想到米勒的那句话:“我把自己建立在悲哀的基础上”,米勒是善良的,他的《拾穗》《晚祷》《播种者》……都充满柔情,他对人类的爱是以忍受苦难的方式显示的,20世纪90年代的诗人汤锋却多了一份沉重。
这匹天马在驰骋中向下俯瞰,看见了似假而实真的人世的全方位景观,于是有“悲壮的发现”:
在一个虚假的梦中真寐
我突然看见从未看见的彩凤和金龙
……
我在悲壮之中发现
战争还不是地球最危险的信号
集体麻木与灵魂疲倦是危险中最大的危险
——《突然》
他发现的是“最大的危险”,我们知道,与此同时,他已将与集体麻木和灵魂疲倦的生死决斗作为义无反顾的使命,他已别无选择:诗就是他手中的武器。对于历史的无知可能造成一个诗人的致命弱点,许多缺少警觉的人退化了,枯萎了,汤锋却不是这样 :
八十年了,一支旱烟还来不及吸完
一个民族的历史即将脱稿
我读着它
如夜鸟飞过山角听见空谷中回音的深沉
——《乡村老人》
他捕捉历史并加以审视,追踪历史并谛听遥远、细微的历史脚步的回音,因为我们都不能不生活在历史的巨大动力里,诗人应该是能够承受,运用这一动力的强者。汤锋的诗里不止一次出现“精神饥饿”这个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活着,我们有太多的话想说
金钱的尺码怎量得准精神饥饿的距离
——《春天的事情》
诗人是有理由骄傲的,以金钱为尺度的世俗奈何不了他。因为有金钱的尺码无法丈量的精神饥饿的距离——有人恬然,昏昏然,笑嘻嘻地享受着精神饥饿给予的陶醉,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了,而诗人活着,却正因为有太多的话想说,这样就有了现代人的思考,现代人的诗,现代史的回音。
二
诗人一直在探寻塑造作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和作品的风格特征的道路,他不停地问自己, 哪一条道路通向真知 :
大地上,凄楚的叹息已停歇下来
时间的倒影已安静下来
有什么向前移动着……向前移动着
飘渺中历史的褶皱已被上苍之手抚平
寂静来临,群峰的翅翼渐渐收拢
亲爱的灵魂在极度的疲倦中朝向神明
钟声响起,团结者在聆听
在山那边道路的期待里
在阳光隐退后月华上升的曼妙中
无声的承诺圣曲一样逼近我们布满尘埃的笑容
——《寂静之声》
现代人的历史课题:人类将朝哪条道路走下去,甚或,有没有道路。不必嘲笑那些歧路彷徨的人,该嘲笑的是那些索性躺下来闭起眼睛塞住耳朵得过且过的自渎者。当代诗人、特别是中国诗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大声疾呼,以期唤醒麻木了的众生,而我们见到的却往往是传播和美化麻木的诗人,可疑的诗人。并不是提倡所谓的多愁善感,无愁无感者能制造的可能只有文字垃圾。诗人在这里寻出了探寻的艰难曲折,在凄楚的叹息、极度的疲倦中,得到的只是山那边道路的期待。朝向神明,无声的承诺已逼近“我们布满尘埃的笑容”, 读到这里,眼睛不为之湿润是不可能的,生的凄迷,生的挣扎,生的哀痛,好像是希望实际是绝望的“神明”的“无声的承诺”是实有的呢 ? 还是虚幻的 ? 这里就有诗,现代中国人的诗。诗人苦苦寻找方向, 却常常发现那方向“混沌难辨”。
那一束喜悦的流浪之光
在我悲戚的命运中
照亮了一个混沌难辨的方向
——《美》
这里就有痛苦。在用痛苦构建性格的过程里,诗人成长, 个性日趋鲜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16年多了”, 见到的是一个又一个“伤口”, 难怪他“猛然发现 : 我来到这世界是这样的匆忙而又孤独,而且,又是那样的无奈而又富有激情”(《在闪烁着诱惑的伤口里》 ——代后记),难怪在他的诗里有这样引人注目的鲜明个性,当代中国诗坛最缺乏因而也最可珍贵的个性,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竟然忘记了诗人首先必须是个个性鲜明的人。古代诗论家所谓的“性情中人”, 诗坛上熙来攘往的竟是一串串相似的面孔,说得苛刻些,此等“无面人”也就是“无心人”,成为“无心人”是由于“无生命”,对生活失去感受能力或根本就不敢感受生活,躲避感受,然而诗人是必须袒露个性——性情的,必须以他的作品向我们昭示一个完整的人的。或许你想要问:为什么诗人有这样多的辛酸 :
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缺少
消逝的主题:深蓝色的星空下
黑暗的父亲正在追求光明的母亲
什么都可以拥有,就是不能再多一个
存在的主题:暗红色的心脏里
再也装不下另一种酸咸的液体
一切都在飘零,一切都在孕育
生命如一堆渐燃的篝火
在记忆和想象的顶峰
将灵魂的障碍物烧成了天蓝色的灰烬
——《消逝》
当诗人的颤栗不可抗拒地以这些诗行传导给你时,带电的语言对你的心灵的冲击是如此猛烈,于是你突然清醒,突然发现你多少年的浑浑噩噩一下子消散,你发现诗人的辛酸和你的辛酸是如此接近,在颤栗中你感悟到思考的力量,诗的力量,你知道了什么叫做“知音”,应该说这才是诗的功能的最佳显示,诗人是会为此感到欣慰的。
十多年来,“无奈”这个词很流行,确实有那么多人生活在无奈里:
有一天我才突然明白
我是强迫自己在一个原本没有答案的地方
寻找答案。这种答案的名称
就叫做无奈。无奈就是终点
就是这个世界和它的主人们
永远的起点
——《春天的事情》
无奈,有鲜明的时代感,历史好容易产生了无奈,无奈是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的生存状态,深重的灾难推广着无奈,生活在无处不在的无奈里的人们甚至没有无奈感。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自己在无奈中已经生活发这么久,而且依然在无奈中,无奈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起点,也是终点,这就是痛苦,巨大无比的痛苦,应该孕育出我们时代的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作为诗人,汤锋却总是不可避免地有那么一点迷茫,那么一阵彷徨,有总是摆脱不掉的忧郁。
未来是什么?未来只是一种方向
那就画一个方向吧
方向是一个没有序数的地方
那里有真理在晨风中飘来荡去
也有一阵发誓不再苦等什么的风在等待另一种风
难道尘世就是风挖掘出来的陷井?难道
这陷井的功能就是在快乐中制造创痛
难道快乐会成为左手,痛苦会成为右手
如果我用这两只手画自己
我又怎么忍心画好一张忧郁的面孔?!
——《自画像》
因为他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必须与无物之物作顽强的搏斗,他必须跌倒了再站起来 :
我匆忙前行,有时也会弯腰拾起光阴
没有谁知道我在跌倒时的重量
更不会有人知道我爬起时的苍茫
——《在光阴中往来》
于是他在苍茫里奔跑,我们听到宽阔的旷野上传来的呐喊者的声音:我们时代的诗。有时, 诗人的思想让我们觉得有些“可怕”:
白天是虔诚的观众 , 它的观望
使大海提供我们伟大的联想:生命的舞台其实就是
一个埋葬着罪恶与丑陋的古老墓场
——《舞台》
大海广阔的颤栗带给诗人无穷联想,被诗人形容为“伟大的”, 伟大在于联想的结果竟是生命的舞台= 古老墓场!不能认为诗人是在有意用惊人之语耸动听闻,可能因为我们看惯了那些小巧玲珑的“精品”和矫情的附和之作,对于沉痛,对于悲悯,对于锥心刻骨的自省倒反感到不那么亲切了。30年代中,柳亚子先生《田星六‘晚秋堂诗集序’》里写道 :“感世运之靡常, 念民生之日蹙, 丘迟才尽, 杜陵泪枯,余固不暇为雍容雅颂之声也。”亚子先生无愧为血性男儿, 忧时之士,他是深知诗人必须是祖国之子,人民之子,时代之子的,可以相信, 诗人汤锋和我们的理解是一致的。
诗人似乎急于找到一条超脱之路:
这是我自我分裂后接受甘露的地方
沿着这条长河,我有勇气启开肮脏的
记忆。我要替代一些猛然回头的人
在圣水中忏悔,并且用尽
所有的言辞所有的血,和一个世界
在创造与毁灭中日渐加大的风暴
除了忏悔,我几乎无事可做
……
这条长河安静地流淌
我一直想沿着水流的方向抵达某个地方
亲爱的上帝请你把我一并带上
——《抵达》
诗人是用痛苦喂养自己,是从痛苦中获得教养的:
我们这一代人从没有硝烟的搏击中活过来了
历史用沉默的眼睛看着这一切
精神的饥饿是我们无法逃避的特殊功课
——《春天的事情》
与这相对照,我们还有那么多像鲁迅先生所说的,自以为生活在天堂里,坐在上帝的脚下,成天吃着糖果的“幸运儿”,高兴时就玩玩诗,终于无诗,因为无所谓精神的饥饿,甚至没有精神,而精神就是思想活动,是思考的存在形态,波特莱尔以来这100年的现代诗已是思考的诗,以思考方式抒情的诗。
痛苦甚至是不可缺少的:
痛苦是一种弥漫着黑色液体的东西
因为迷人的画面上不能缺少这种色泽
因为一味的幸福同样容易让人产生疲惫
——《痛苦》
痛苦这黑色的液体是实有的,而幸福的色泽只能代表虚无,只存在于想望之中,不可能没有想望,但不能是“一味的”,因为虚无不有代替实有而只能“产生疲惫”。这就是诗人的哲学。读完汤锋的这部诗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以探寻道路的迷茫,辛酸,无奈,忧郁……迭加起来的痛苦塑造他的思想者性格,是从这条路上向诗歌艺术的终极——大气走出去的。大气磅礴,应该是现代诗的本性,现代诗先天具有的素质。
汤锋的诗路历程告诉我们 : 个性的获得只能来自生活的严峻考验 :
我用我不灭的热情把时间点燃
让遗失在土地中的誓言和孤独
燃烧 , 借夜晚的力量添加
善良的干柴和幻美的想象
……
岁月的隐痛一如灰烬 , 我已在未来的宁静中
留下姓名 , 凝望一缕缕温暖款款上升
我懂得在冬季该怎样去承受刺骨穿心的寒冷
——《伤痕》
请注意 : 诗人在这里又一次使用了“灰烬”这个形象 , 应该说 , 这是很自然的 , 对于他 , 生命的历程就是一次接着一次的连续不断的燃烧 , 难怪有这么多频繁的颤栗 , 是生活的加害呢 ? 还是生活的赐予? 我想, 对于诗人应该是后者。龚定庵诗:“不是无端悲怨深,直将阅历写成吟”。阅历应该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路历程(而不是所谓的“生活积累”,文艺创造毕竟不是事务性操作),对于汤锋,痛苦才是安身立命之所。
谁最了解世界的原貌?谁最痛爱
在群魔的舞蹈中折伤的筋骨和脊梁?
谁是万物的亲人和恩人呢?啊
告诉我神祗莅临尘世的每一个瞬间和地点
请把你透明的回答写在夏天的藤蔓上
我要在日趋沉静的思辨中推敲岁月的内涵
风口阿,慈爱和美意的传播者,你为何要把
纯洁和高雅的力量散发在大地胸膛?!
——《风》
思想者是受难者,他只能在苦苦求索的无尽熬煎里一点一滴地消耗自己的热血,他太纯洁太高雅了,只知道心力交瘁地推敲岁月的内涵,忘记了折伤筋骨和脊梁的痛楚。我想说,这才是诗,是我们时代的最强音。这是有我们时代需要的,能凸现我们时代精神的大气,至少是能供我们接近这个大气的征兆,这里有我们的诗人应该向往的伟大,应该追求的不朽,也许这只能算是一个开始,但我们必须记住: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这就是汤锋为我们画的作为思想者的诗人的画像:
诗人在旅途为一些小事情
折磨肉体。为一些原则问题
折磨灵魂。他的两个眉头
一个为自己而皱
一个为世界而皱
——《诗人》
在漫长的人生之旅中,这些自愿的“殉诗者”不断地受着内、外折磨,外的折磨被当作“小事”,因为肉体的折磨对于诗人简直不值一提,而内的折磨则是原则的,有值得深深体味的多种痛苦,诗人们就是这样紧皱眉头悲壮地跋涉在从生活的炼狱到诗歌的祭坛的路上。
看吧,诗人自豪地宣告了:
是我需要宣泄还是黑夜需要宣泄
……
在没有路的路上匆忙焦灼地散步
我被诗歌骄傲地堆成了黑夜的巨人
——《散步》
需要宣泄,这就成为“黑夜的巨人”,这巨人,是“诗歌骄傲登地堆成”的。
三
汤锋的诗是新的,新到使你惊喜,使你好像发现一条通向新的世界的新的道路而永难忘怀:
我坐在蜂的薄翼上张望和歇息,我发现
我还在吟唱昨夜的疲倦和明天的奇迹,有什么
在花丛中闪烁:那疤痕怎么会这样美丽而沉寂?
——《疤痕》
这里,没有时下流行的毫不相干的各色奇形怪状的“形象”的胡乱凑合,没有混乱的破碎的词语的突兀堆积,更没有“反文学”、“反语言”(或者相反:“纯文学”、“纯语言”)的标榜,“探索”、“实验”,事实上和严肃的探索、实验相去甚远的文字游戏。汤锋是清醒的,他没有随波逐流,读他的诗,我们能明白用牺牲诗的素质,甚至离开诗的崇高本质去追求事实上与诗无关、甚至有意无意地冒犯诗亵渎诗的“新潮”,文化的低层次有一种叫做“流行”的现象,各类“新款”交替出现的奇装异服,无奇不有的发型表明的只能是某些人的内心空虚和趣味低下,不料这种风气近20年来居然流行到一部份新诗作者中,导致了混乱,停滞和读者的厌恶。幸而,像汤锋这样的严肃的诗人们正在用他们的作品示范性的对这种颓废和倒退雄辩地进行驳斥。上面引用的这三行诗里几乎没有“新潮”的痕迹,然而绝不陈旧,而具有能给人以震撼的新,原来,新不在于“包装”,更不在于用广告语言(原谅我可能说得有些过份了)“推销自己”,而在于真诚的内心袒露。试想,如果这三行诗哪怕多那么一点点“花俏”,还能这样感动人吗?
对于汤锋,求新是艺术创造的根本要求和神圣职责:
轻轻地我来到世界的大门前
我敲门的手被风抓住,我张开的唇
被无声之声堵塞。我的心
被自己的疲惫压得只剩下微弱的跳动
这时候,我突然听见守门神说——
你就是你自己的谜,我也正准备
去敲开你关闭着整个世界的眼睛……
——《这个世界》
诗人构建的新的境界给我们以强烈持久的震撼,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有什么更好的表现方式可以替代它。“我”的形象在短短七行诗里悲壮地屹立在我们面前,显见功力之不凡,然而没有一点“怪”,没有故作惊人之笔。一个诗人的悲哀往往由于想轻易地取得“轰动效应”而丧失自我,成为“一片浮萍。查初白诗:“自笑年来诗境熟,每从熟处欲求生。”熟是一条老路,生是一条新路,诗人努力于发现新路时还是站在熟路上的,走上新路不是突然变成另一个人,那样就会是个性的丧失,而个性正是一个诗人的灵魂之所在。这七行诗是新的,而汤锋仍旧是汤锋。
读汤锋的诗有时会感到咄咄迫人,有一股凌厉之气,简直叫人受不了:
在无始无终的道路上
谁的脚步已经忘记它在四处流浪
灵魂在不断地把尘埃收藏
紧接着,斜坡渐陡,痛苦向阳
一群准备飞往教堂上空的鸽子突然失去方向
一只懂得什么叫做沧桑的天鹅
和一朵没有泪水的玫瑰相遇了
它们一边相亲相爱一边要去驱赶烦恼
而烦恼是命运之神赐给快乐的伙伴
在大雪尚未到来之前,在精神宫殿的隔壁
孤独也奔腾而来,孤独不讲道理
它以统治者的身份出现
永远地居住着,它一次又一次对准烦恼大动干戈
月亮在这时有了充分的理由走向麻木
太阳的照耀完全是为了我们的不知所措
看不见的债务也要把我们挽留
然而我们还是像犁铧翻动贫瘠的土地
像万物终于摆脱了漫长而泛滥的雨季
我们以伟大的英明收获了苦难的爱情
以女神般的力量收获了无家可归的善良
——《世界的旅馆》
然而你不能不喜爱它,不能不受感动,这位骨科大夫太严厉了,不顾几乎会令你晕厥过去的剧痛,猛力一击,把你那脱白的关节接合拢来,而你永远不会忘记行手术时他那专注的眼神里慈母般温柔体贴的爱意。诗人永远是善良的,对不公正的深恶痛绝正是来自他对人类的深沉的爱。诗人不是什么心理变态的恨世者,他的苛刻和夸张都是善意的。当毕加索说“我是来反对的”时,不必急于认为这是个破坏狂,因为接下去我们还必须证实他的这一句话:“先反对,后赞成”,没有什么,他只是不愿意随声附和。诗人们并不自以为他们是立法者或执法者,只是不愿意做一个冷漠的旁观者。诗的本性所具有的使命感让他们不能不是这样的,自然而然地是这样的。
除了美,诗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还能追求什么:
未来世界的梳妆镜前
我细心端详着你的脸你的眼
我猛然发现:你的五官
在局部分别诉说着尘世的凄迷
又整体表达了世界不可抗拒的美丽
我为什么要和你邂逅?你为什么
会让我在前世纪的记忆中发现今生的奇迹
——《热爱》
然而这美却是沉重的,沉重到诗人不能不在欣幸之中连续问两个“为什么”?从镜子里映现的“今生的奇迹”——“不可抗拒的美丽”却又和“前世的记忆”紧紧连结在一起,历史的宿命让这美沉重,以前世纪到本世纪,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走过的是何等险厄的生死存亡的边缘上的没有路的路,我们闯过来了,终于有了“今生的奇迹”,这奇迹是美的,然而又是凄苦的,悲剧的美,能够发现它的只有真正的时代之子。
汤锋的语言是美的,有水一般的清澈和深情的流动:
水要到远方的沙漠去
它要带走崇高的生命是那么大方而感人
在最柔弱和最坚硬之间,它统治着人类的渴望
并教给世人奉爱的寂寞和忏悔的虔诚
——《水》
海伦·凯勒说:“思想使语言美丽。”读汤锋的诗,对于语言的美,我们能省悟到这美是怎样来的,我们怎样才能得到它。诗人没有被时下流行的雕琢堆砌之风所迷惑,他鄙弃粉饰,努力于从思想的本真和语言的本真的契合去发现并保卫美。20年来我们的作者群(绝大多数是有才华并忠诚于诗的)在一种不健康或不很健康的风气里不自觉或自觉地偏爱,甚至沉溺于语言——文字游戏,追求“痛快一时”的轰动效应,结果是浪费了才华与大好光阴,不少人终于不能不带着遗憾离开诗。读汤锋的诗,我们能记住:思想的美是第一位的,作为思想的载体的语言是第二位的。
四
诗人汤锋的创作活动开始于80年代初期,那是一个使人奋发的文学复归时期,人们发现多年来生活在失去文学的贫乏里,濒于枯萎的心灵很快地复苏了,以新诗为前导的新文学开始回到生活里,和他的众多同辈作者一起,汤锋被卷入以创新为主要努力的浪潮里。创新无疑是文学不可缺少的生机,然而文学先天地是精神活动而不是或不完全是技术性操作,历史形成的诸多因素使新诗的大部分作者偏离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传统,堕向唯美主义——形式主义魔障,造成了将近20年的徘徊。不同于他的同辈,汤锋在不断的思考中坚持走自己选择的道路:真正的现代性和民族性的道路,他要写的只能是现代中华民族的思考,痛苦成为他的诗的主调,因此而落落寡合,但他不怕孤独,淡泊朝市上的名利。对于他,写诗几乎成为自我折磨,而这折磨里却有大的欢乐:
我的胸口为何常常冰凉?常常隐痛?
我为何在寻找方向时总是害怕失去自我
我为何总是望着前进的倒影沉默无语?
告诉我,道路,你是不是在时间的伤口里苦苦等我?
……
心中的慈爱是这样辽阔而永恒
我沧桑的大腿怎能迈出悲悯的内心
——《描绘》
自我折磨就这样伴随着诗人自觉自愿的自我放逐,我们竟难分辨他唱的是痛苦之歌还是欢乐之歌,我们却相信冰凉胸口的隐痛并没有使他止步,愈是执着于肯定自我愈是能保有自我,寻找方向的道路上前进的倒影给予的启示太多了,只能沉默,在沉默中咀嚼这些启示。当时间的伤口终于出现苦苦等待他的道路,诗人问自己:“我沧桑的大腿怎能迈出悲悯的内心”,我们能体会:他是一定能迈出去,而且永远地走下去的,因为他“心中的慈爱是这样辽阔而永恒”。很少读到这样大气磅礴的诗了,我们期待着新的惊天动地的力作的出现。
诗人,请接受我的祝福,中国新诗,请接受我的祝福。


彭燕郊,原名陈德矩,“七月派”代表诗人。1920年9月出生于福建莆田黄石。1938年后历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宣传队员,军战地服务团团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常务理事、创作部副部长,《广西日报》编辑,《光明日报》副刊编辑,湖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湘潭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彭燕郊诗选》《高原行脚》,评论集《和亮亮谈诗》,主编《诗苑译林》《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外国诗辞典》等。


汤锋,原名:汤学锋;湘人;笔名奔马、茹阿玛。曾就职于深圳《金融早报》、湖南毛泽东文学院。在《诗刊》《十月》《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近千件;作品并收载于《中国诗歌年鉴》《作文学》《散文选刊》《新华文摘》等书刊;获得各项评奖十余次;著有诗集《亲如未来》《内心的闪电》。现居湖南长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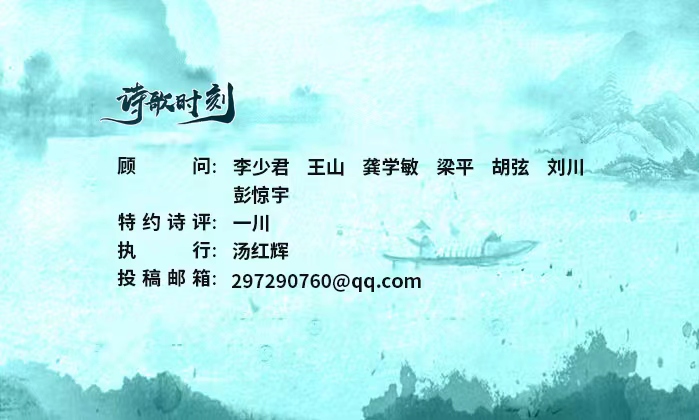
来源:“诗赏读”微信公众号
作者:彭燕郊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