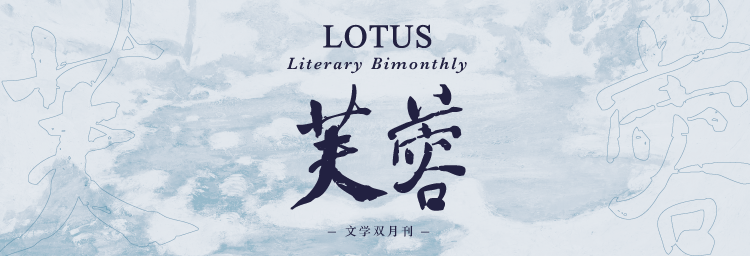

莫克/摄
夜空尽头的星(短篇小说)
文/罗志远
我第一次拖着行李来到这里时,只见约五平方米的空间里除了一张简易的木质床、一把椅子和一张靠窗的桌子外,只有一台安在侧墙上的老式空调。
房主拿着钥匙打开房门,领我进来,指着房间说,这就是你的房间了。我环顾四周,只见分别紧靠前后墙面的桌子和床已经接近占满空间,留下一条可怜巴巴的小道,仅能过身。我把行李扣打开,找出准备好的床单铺上,台灯和备考的书本放在桌上,交完押金和房租后,除去吃饭的钱外,钱包的钱所剩无几。房主交给我空调遥控器前,我说空调的滤网脏了,要取下来擦洗一下,酷暑或寒冬,十分需要。她暗示我,之前有好几个租房的学生都没有擦,这不是什么费劲的大事。我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她留下钥匙,离开前,主动帮我把门带上。我站在门口,望着面前狭小的房间苦笑,这就是未来半年我要待的地方。
租房的钱是我过去四年做兼职攒的。之所以没有选择待在家里,也许是受不了父亲坐在沙发上一次又一次的唉声叹气,或者是受不了母亲洗碗时反复的唠叨。墙上的挂钟嘀嗒走着,时间格外难熬,因为考试失败,那一段时间,我只要在家里走动,我的呼吸本身好像也成为错误。起初我抱有侥幸,待在自己房间,昏天黑地地睡觉,以为这样可以忘却一切失落情绪,摆脱一切外在言语。直到有一天,母亲猛地掀开被窝,开始新的一轮指点,家里不是养猪的,吃了睡,睡醒了吃,你看这都几点了,人要有上进心,你都这么大的人了,以后怎么得了。
我想很大声地争执一番,在脑海里翻江倒海搜刮几个词,可我如泄气的皮球,力气早在最后那次出成绩时消耗殆尽,声音越来越小,最终我们不欢而散。我没有勇气辩驳母亲半是埋怨半是讥讽的话语,更没有底气去面对她日益苍老的面孔。她打小儿就教育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好好学习才有出路。母亲给人洗了半辈子衣服,直到被洗衣机所替代。在她眼里,教师、医生、公务员才是体面的职业,除此之外,其他都不算正经工作。父亲白天在外务工,还未回来,他早已到退休的年龄,缴完社保,还要养一个家,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像一头老牛一样,拼命做事挣钱,并且受限于年龄,没有挑三拣四的余地,哪儿有活儿去哪儿。
考试与成绩,从来都是连在一起的。其实不只是父母,亲戚、邻居,以及很多过往几乎没有接触过的人,在考试结束后,都一一冒出来,专程问询成绩。譬如吃年夜饭时,亲戚围坐一桌,工作和婚姻,经济和医疗,不论从什么话题开始,最后总能绕到子女教育上,那时我尚可以用成绩还没出来当作盾牌,埋头啃着鸡爪,装出漫不经心的模样,可一旦尘埃落定,连自我辩驳的机会也不再有。他们询问的语气相差无几,态度貌似和善和热心,借着打电话拜年之机,有意无意地问询。母亲敷衍,只说差几分。接着亲戚就会发出几声叹息,说真是太可惜了。紧接着还没安慰两句,又问询下一步的打算,又或者目的已经达到,把话题引开,说两句便挂断。当然,更多时候,他们会把那些遥远的姐姐妹妹哥哥弟弟一干拉扯进来。出国的,上名校的,月入多少位数,贴满各种光鲜的标签,啧啧称赞,反令我更感压抑,在那一刻,那些人不再只是我的亲戚,而是同我相比较的参照物,给我施加压力的秤砣,压在我的肩背上,让我喘不过气来。一旦我抱怨起来,干嘛总要把我的具体情况说出去,母亲便会装出没什么大不了的模样。
“哎呀,这是你亲戚,小时候抱过你的,和她们说没什么的。”
家里有三个人,我却成了最格格不入的那个。毕业、工作、恋爱、结婚、生子。晚饭桌上,我们讨论着这些话题,按照父母那一代人的想法,我人生的轨迹应当波澜不惊宛如一条小河,流淌在既定的河道,但这从来不是我想要的。
某一天,我鼓足勇气,提出想再考一次。挂在墙上的钟有条不紊地走动着。屏幕上的主持人西装革履,正郑重介绍着关于市场即将迎来新一波大学毕业生求职热潮。尽管我已经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但那冷嘲热讽的语言还是令我受挫。这是血缘上与我最亲的人对我提出的疑问。母亲一遍遍敲击着碗筷,指责声如雨点般落下,父亲的手掌高高扬起,又重重拍在膝盖上。他的大拇指早年上工时,被支架砸到,早已发黑坏死。家里没有试错的成本,而我已经丧失唯一的机会。
当晚,我回到房间,呆呆看着摆在书桌一角积尘的复习资料。这些书本,自考完后,我没再碰过。纸上抄满密密麻麻的文字,文字上画满红蓝线条,书角贴着一张又一张贴纸,以此标记重点。明明之前我告诉自己只要拼尽全力,便不会留遗憾。当我再次翻开这些资料,却依旧感到一种抹不去的委屈在心头溢开。
校园招聘会即将过去,那时我还未正式毕业,父母每天催促我回校后要多注意注意,或者不知从哪儿找到一大摞招聘广告摔在我面前。上面微薄的薪水数字和繁重的工作打碎以往我的幻想。家里的每一寸空气都如此沉重,为避免琐屑的言语,我选择白天尽量出门瞎转悠。有一次回家,换鞋时,我在门口无意间听到邻居阿姨在和母亲聊天。
“×××家的闺女考公已经考五年了,几千人报考,本来初试第一,复试被刷下来了,准备第六次备考。”
“只招一人,哪怕多一个也好啊。”
话里话外止不住地叹息。也许是这句话触动了母亲的某根心弦,她虽仍一个劲唠叨,但指责声变小了。而我回到学校,仓促毕业离校。从宿舍楼搬出来前一天,我抱着侥幸的心理,专程跑去图书馆一趟,尝试用以往的方式进去。
“嘀——身份无法识别。”
我手握着失效的学生卡,苦笑。果然如此。
同一天晚上,我胸前揣抱着书包,兀自坐在楼道的台阶上。四周格外漆黑、格外寂静,这一带的衣服全收光了,一片空空荡荡。我透过铁栏,看着遥远的天际那几颗若隐若现的星子,散发着微弱光辉。也许不回去的决定,就是在这一刻下的吧。
取消返程的车票后,我发了一条含糊其词的短信过去,却被敏锐的母亲一下察觉到了。她一连来了几个电话,劈头盖脸一顿问,真的还要考吗?这一次真的考得上吗?我感到不知所措,不知该怎么对她说。是的,邻居家的孩子考了五次还没考上,我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行呢?我和母亲在电话里一阵沉默,双方迟迟没有说话,就在我的勇气濒临瓦解之际,母亲突然说了句,算了,你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吧,反正长这么大,我也管不了你了。然后嘟的一声挂断电话。我拿着手机,呆呆站在原地,心底暗暗松了一口气,同时还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在蔓延,毕竟她并没额外说些什么,但除此之外,我还希望她说些什么呢。
甩掉一切无用的想法,我花一天时间一连看了好几间出租房,最后顺利在教职工楼找到一间。也许冥冥中有安排,三间房间,其中两间已被预订,只剩下最后一间。
因为是平摊,房租不算贵,除我之外,其余两个租客也是女生。我们互不熟悉,各自在自己房间备考。共用一个客厅、厨房和卫浴。房主临走前,悄悄告诉我,她们也都是“二战”。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去厨房做饭,多是点外卖,或者单独出门吃,上厕所也会很默契地分开时段,听到冲水声,隔一段时间会蹑手蹑脚去看,要是没人,迅速溜进去蹲下身,松一口气。电视机成为摆设,平日客厅静悄悄,若有窃贼撬门进来,大概会怀疑这是一间空房。桌前,我们每天的任务是做题,做大量的题;看书,看各种枯燥无味的专业书。我们在这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上搏杀、较劲,啃着笔帽,苦挠头发,各自打着一场无声的战役。桌上方的窗户外藤蔓缠绕,大概很久未修理了。每当看书看得累了,我总爱揉着酸痛的肩膀,来回摇晃腰板。屁股下的椅子是另配的,底下安了四个轮子,身体稍一动就会咯吱咯吱叫。我瘫在座位上,遥望近在眼前的天花板,却总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错觉。于是转移视线,凝神细看那些窗前的藤蔓,透过新绿,窗外下方是一条笔直的小路,靠近学校后山的人工湖边。有一次,一对情侣在此驻足,热吻。我呆呆地看着这一切。未等回过神,一块石头愤怒地扔来,砰的一声,撞击到窗前的铝杆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他们离开了。
更多的时候,窗外一个人也没有,连风也静止了,房内房外只有自己。因为屁股下的四轮椅子坐着不舒服,我改换成普通座椅。于是咯吱咯吱的声音不再响起,房间安静许多。床就在身后,一回头就能看见,哪怕只是简单的木质床,此时也充满诱惑。复习之初,学累了,我捧着书躺上去两次,脑海里反复记忆着刚看过的知识点,一面心底默念,只是休息片刻,千万不要睡着,另一面自我的意识却沉入睡眠。醒来后,我首先感到恍如隔世,紧接着是一种强烈的负罪感涌上心头。唉,这一下子浪费了多少个钟头,放在书本上,能学到多少内容。从此以后,白天我再也没有躺上去过,哪怕只是挨一下床板,也要赶忙坐起来,怕一下又睡过去。
连续学了好几个小时后,当我再次拿起书本时,明明上面的每一个字都认识,但始终进不去脑子里。好像有一道无声的指令,无情地告诉我,今天的脑容量已经饱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抱着书发呆,心底暗想,那两个女孩在做什么,是不是此刻和我一样拿着书,感到为难,又或者写个不停,一支笔芯用完,接着换上另一支。
(节选自2023年第6期《芙蓉》短篇小说《夜空尽头的星》)

罗志远,1999年生,湖南长沙人,本科毕业于西南大学文学院,现为西北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在读硕士,作品散见于《作家》《天涯》《西湖》《湖南文学》等。有小说被《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已出版小说集《书法家》。
来源:《芙蓉》
作者:罗志远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