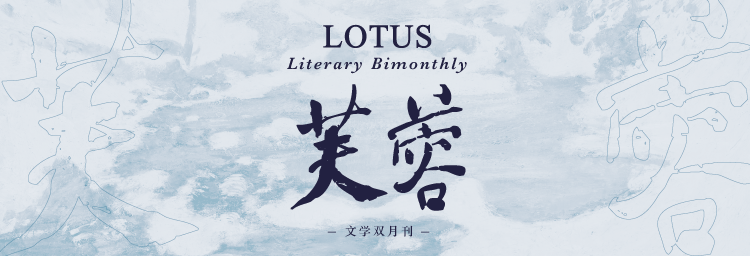

深秋已过(短篇小说)
文/罗志远
一
柜台上的盒饭早已冷了,李铁刚扒了两口饭,看见玻璃门被推开了,唐咏准时走进来。
下午五点,诊所没什么人,地面刚被拖洗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味,老式电视机里有气无力地传出几句新闻播报的声音,几个老人瘫在座椅上,挂着吊瓶,一概在闭眼午睡。外面可能在下一场小雨,唐咏的衣领口像浸了几点油墨,散点式洇开,脸颊上是细密的水珠。她绕过一个个老人,径直来到李铁面前,还没等开口,李铁用下巴努了努手上捧着的盒饭,又指了指空着的位子,示意她先坐。他看到面前的唐咏头发湿了,于是去里屋拿了一条毛巾,递给她后,继续捧起盒饭吃。
一份盒饭,李铁吃了半个小时,中途唐咏没有催,也没说话,坐在对面,低头看着方形地砖,用毛巾一次次擦干头发。吃完饭,李铁把两个空餐盒整齐码好,收进塑料袋里,然后去卫生间洗了个手,回到柜台前。他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中药包,交给唐咏。他说,他最近怎么样了?唐咏摇摇头说,不见好,还是老样子。李铁说,放宽心,这病没法儿根治,只能慢慢缓解,坚持着来。李铁又安慰说,干过这一行的都一样,好好养着吧,记得下个月再来取药。唐咏点点头,嘴唇抿紧成一条缝,脸颊苍白,眼皮底下有两个黑眼圈,看起来神色憔悴。她出门前,李铁专门喊了一声,外面雨停了吗?许多时候,雨并不能被肉眼所见,只能用身体去感受。唐咏伸出一条胳膊,并没有感受到雨滴落下,朝后点了点头,然后一条腿跨出门去。李铁紧跟其后,也出来了,只不过唐咏是朝东,家里还有一个男人等着她,而李铁手拎着塑料餐盒,往北直走,对面不远处就是垃圾站。
丢完垃圾,回到诊所,李铁注意到唐咏用过的那块白色毛巾掉落在地上,他走去捡起来,放在鼻尖嗅了嗅,有一股淡淡的发香。他拍去上面的灰尘,走去卫生间,把毛巾搓洗干净,洗完后挂在衣架上。他回到柜台的椅子重新坐下时,几个老人已经醒来了,其中一个甚至把视线扫向他,但他没有回应。他从抽屉里找出笔记本,翻到最新记录的页数,勾去唐咏的名字一格。如此一来,在预约的一干名字中,唐咏这次就算正式取药完毕。而这已经是唐咏第十二次取药了。
诊所来去这么多人,李铁犹记得第一次见到唐咏时的情景。
去年今日,同样是一个初秋,门口的叶子却早已泛黄。李铁在门口扫着落叶,因为叶子很多,他一遍又一遍扫着,突然看见一个女人迎面朝他走来。女人身材娇小,头发垂至耳梢,脸上戴着一副白色口罩,虽然看不出具体年纪,但露出的眼角已有几道鱼尾纹。李铁认出她所穿的那件蓝色工装来自附近的纺织厂,显然,她是一名纺织厂工人,与此同时,她还搀扶着一个男人。那个男人面容苍老,手握成拳头,放在嘴巴边,不停地咳嗽。这是他后来才注意到的。
“看病?”李铁问。
女人点了点头,并指了指身边这个男人。李铁收好扫把和簸箕,把玻璃门拉开,请他们进去。并没有费什么工夫,甚至用不到什么专业仪器,先看男人蜡黄的面容,然后让他伸了伸舌头,李铁已经大致明白一切。即便如此,李铁还是多问了一句,干什么的?没等男人回答,女人已经开口,在化工厂上班。李铁说,化工厂不是刚刚改制了吗?女人说,嗯,之前在,他刚下来,现在还在找事做,也不知以后还有没有地方要。
女人摘下口罩,李铁凝视了两秒,又看看她身边的男人,没再多问。这一年来,他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人到中年,从工厂出来,带一身的病,无处可去。而化工厂又属于重灾区,成天在弥漫工业粉尘的环境中上班,吸入的粉尘在肺内沉积,咳嗽是常态,一旦不注意,更容易发展成肺炎。
他开好药,打包递给这个名叫唐咏的女人,因为是慢性病,他和唐咏约定好取药时间,一个月一次。这时玻璃门被打开一条缝,一个小女孩钻进来,扎着双马尾辫,手里拿着一根剥开糖纸的棒棒糖,一下扑到唐咏怀里。
唐咏指着李铁,让小女孩叫叔叔。小女孩便喊了。李铁看出这是他们的女儿,不仅因为两人的亲昵举止,还因为两人相貌相像。尽管年幼,小女孩的眉眼已有几分像她的母亲。他努力扯动嘴角笑了笑,尽管长期以来,他并不习惯这个动作。过去有很多病患,一次次朝他诉苦,甚至哀号,他都面无表情地听着,顶多嘴上安慰几句。大概他从来都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以前是,未来也会是。加之,作为一个职业医生,生离死别他已见过太多次,可能上周一个一顿能吃两大碗米饭、面色红润的病人,今日已经被埋进泥土。所以不论多么痛苦或者喜悦,他已习惯把个人情绪深深埋藏在心底。
唐咏付过钱,一张,两张,都是带毛边的钞票,随后再一次搀扶起她的丈夫,下了椅子,一步步朝门的方向走去,但因为两人身形并不匹配,所以走得摇摇晃晃,像是一长一短两根不稳的木头,彼此扶持着。小女孩快步向前,使出吃奶的劲,尝试推开玻璃门,步子反而不断往后挪。李铁从柜台后方出来,走去主动打开门,天边晚霞烧尽,稀薄的夕光照着大地,他看着他们一家三口离开。
二
从第二次起,男人没有再出现,每次都是唐咏一个人过来取药。
因为忙不过来,有那么几次,李铁都得现场抓药。金银花、桔梗、枇杷叶、柴胡,李铁从各个抽屉里抓一小把,上秤称量,用纸包好后,唐咏会带回去煎好药,给男人喂服。在唐咏的口述中,男人的症状尚未好转,还是成天咳嗽,且下不来床。对此,李铁不知道该说什么,想额外安慰几句,但两人的对话经常会被打断。
在一排的座椅上,都是这条街上的病人,因为整个诊所就李铁一个医生,每个人都会把麻烦和问题抛向他。比如,有人发现挂着的葡萄糖袋空了,会举手让李铁换新的一袋;有人会捂着脑袋,说自己头晕,请李铁把打点滴的齿轮调慢一点;还有人口渴了,会一遍遍喊着他的名字……李铁只得中断和唐咏的交流,回应不同病人的请求。
几次下来,唐咏再来时,话就更少了,两人逐渐培养出默契,从进入诊所到取药离开,甚至没有一句交流。
在这短短几分钟里,唐咏会一直坐在靠边的位子上,两手放在腿上,安静等待。有的病人要打几个小时的吊瓶,闲得无聊,跟她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这一段时间的话题是,国企改制和买断费,并历数今年以来垮掉的厂子,从化工厂到后来的服装厂,从钢铁厂到后来的纺织厂。当说到纺织厂时,唐咏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好像这件事和自己无关,而李铁早已注意到唐咏没再穿过那件蓝色工装,他不会主动提,而是按照药方,在各个抽屉里抓着药,每一味药材都要尽量避免误差,按克严格称量好,再打包交给唐咏。他还会主动送唐咏到门口,目送她离开。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远处,他再扭头回去,继续面对一拨又一拨在诊所的病人。
李铁不会抱怨某个病人麻烦,也不会假装没听见他们的需求,更不是一个多嘴的人,所以病人都很喜欢他。大家都知道,虽然李铁人过中年,但多年来一直单身,也没有听说和哪个女人有过所谓的绯闻,于是热心地给他介绍对象,但都被李铁一个个婉言拒绝了。见此,大家便识趣地不再提及。
这天一大早,几人又聊到街上传出的一条新流言。近来一个双双下岗的职工家庭,一个素来善良的女人,因为受不了丈夫整日酗酒和家暴,跟着一个卖水果的男人连夜跑了。隔天,丈夫挥舞着一根铁棒找来,四处寻遍无果,弃了铁棒,在大街上脱了衣服,边抹眼泪边哭诉,女人的风评迅速跌入谷底,连带着亲友不敢正脸出门,家门口的白墙上也被人写满各种刻薄言语,难以擦掉。
“现在日子都不好过,有孩子有家庭,有啥困难都得面对,谁跑了,那还要不要脸了。”一阵沉默。一个人慢慢开口,说出大家的心声。
李铁默不作声地听着,拿拖把给地板拖着地,走到病人跟前,让他们抬起脚。
又到了上班的时间,刚才说话的那个人拉了拉旁边那个头发斑白的苍老男人。
“老李,今天还去不去车间干活儿?”
“干啥活儿啊,都拖欠好几个月工资了。”男人回道。
“知足吧,隔壁几个厂,名单都下来了,一个个都得走,这找谁说理去。”
虽然这么抱怨着,但两人还是请李铁过来拔了针管,相互扶着走了。
李铁收好棉签盒,回到柜台后方整理药品。一直到天黑,一个个病人陆续离开,他再锁好诊所的玻璃门,关掉所有的灯。他每天都睡在诊所,这是他的店,也是他的家。
又到了唐咏该取药的时候。
固定的时间点,天色一线的蓝变淡变散,橘黄色一点点渗入其中。唐咏会在这点昏黄色的夕光透过玻璃门洒在地板时,轻轻推门而入。
这天诊所没几个病人,李铁看着那道玻璃门,一个影子逐渐在地上拉长,不出意外,是唐咏。李铁往前走了两步,但又退回来,他假装在收拾玻璃柜台里的药品,看到唐咏走到跟前,才抬起头来。
和上次一样的话语,李铁问,他最近怎么样了?唐咏摇摇头,没说话。李铁看着眼前这个女人苍白的面孔,原本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不知为何,一时竟然无法说出口。短暂的沉默后,李铁照例在柜台后抓药,唐咏照例坐在靠边的椅子上等待,两人间隔大约两米的距离。
最后一个病人离开了,整个诊所就剩两个人。挂在墙上的电视机正在播放一部家庭伦理剧,大致内容是男人的情妇和妻子在争吵,声音模糊,时断时续,李铁走过去把电视机关了,空间一下陷入寂静。他走到饮水机接了一杯水,递给唐咏。喝杯水吧,他说。唐咏两手捧着一次性纸杯,润湿干裂的嘴唇,小小抿了一口,随后紧盯杯中荡漾的水。从他的视线看过去,唐咏的头发虽还乌黑,但发质干枯。李铁大概猜测,她近来睡眠不大好,甚至如他一样,整夜整夜失眠,都有可能。他想起深夜时,脑子里浮现出那个身影,挥之不去,更无法言说。
唐咏接过药包,几分钟过去了,她好像丝毫没有起身要走的意思,只是一声不吭地坐在椅子上,不知在想些什么。于是李铁问了一句,唐咏说她是在等女儿放学路过,然后一同回家,今早上学时说好的。李铁点点头说,明白。这种事在诊所时常发生,妻子等丈夫、父母等孩子、老人等子女,再一块儿离开。两人借着女儿的话题聊了几句,但李铁没有女儿,只有一个英年早逝的妹妹,她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难产死去的那天,丈夫还在麻将馆推牌九。李铁说到一半,看唐咏没有反应,便知趣地止住话题。
黄昏,夕阳把天空染成枫叶的颜色,门口的水果摊传来卖苹果的吆喝声。李铁说,吃不吃苹果?没有主语,但显而易见,他问的人是唐咏。唐咏摇了摇头。李铁还是坚持说,等我一下,我出门买些苹果。没等唐咏说些什么,李铁已经打开门出去了,几分钟后,他回来了,手上果然多了一袋苹果。李铁取出一枚个大的红苹果,把贴着的标签撕下来,但撕得十分慢,怕撕得不好,胶水会粘在果皮上。然后,他把光滑的苹果塞到唐咏手上,两人的手不小心轻轻碰了一下,然后像是触电一般,迅速分开。李铁示意她试一下口感,一面说着,一面把一个小的塞进嘴里。
唐咏把苹果举到嘴边,试探性地轻轻啃了一口,只听咔的一声,十分清脆,果皮上留下两道不深不浅的齿痕,再啃一口,这次加大咬合力,一块果肉咬下来。她开始咀嚼,先是一股酸涩在口腔内化开,后来慢慢变甜了。
两人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还是李铁率先开口。他说,苹果味道怎么样?唐咏说,挺好,很甜。李铁说,那家我熟悉,虽然一直没开正式门面,但口感很好。李铁又递了一个过去,说,再吃一个吧。两个人的指尖再次碰了一下。接过这个苹果后,唐咏低头把玩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两人没再说话。
黄昏的光线从身后的窗台一点点往上挪动,照进半个诊所,照在两个人身上。不知为什么,李铁突然感到有点热,于是解开领口的两粒扣子,与此同时,身子主动向前一步。他看了看门的位置,没有任何有人要进来的动静。
突然,唐咏咳了一声。声音并不大,但在安静的诊所格外清晰。李铁说,你感冒了?唐咏摇摇头说,没有,只是呛到了。他们再次陷入短暂的沉默。
这次是唐咏问,年纪也到了,怎么不找一个?李铁没说话。唐咏接着问,听说很多人给你介绍对象,街上这么多年轻漂亮的姑娘,你就没看上眼的?李铁摇摇头,说,你也是来给我介绍对象的?唐咏说,没有,只是问问。李铁“嗯”了一声,刚要说些什么,一个中年男人头上包着纱布,一瘸一拐地走过来。近来,来就诊的工厂职工陡然增多,不知发生了什么,他们大多带着些外伤,轻则处理伤口即可,重则是被抬进来的。
他闭紧嘴,唐咏也不再说话。两人各自吃着苹果,诊所内,只有咀嚼苹果的清脆声音。李铁感觉到,一咬到果核,苹果的味道就慢慢变酸了。苹果吃完了,唐咏把果核扔进垃圾桶,起身朝门外走去。
这个男人要换一块干净的纱布,李铁把他安置在座位上,看到唐咏已经拉开门,几片叶子随着风飘进来,李铁走到门口去送她。他说,你女儿还没放学吗?唐咏把另一个苹果揣在衣兜里,想了想,说,可能直接回家了。李铁点头说,那赶紧回去吧,别让他们等太久。夕光穿过窸窣作响的枫叶,李铁目送唐咏走远。他突然想到,这是唐咏一年多来,待得最久的一次,以后可能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三
一日,大概清晨五点,天还没亮,李铁出门去菜市场买些菜,发现街边立了一块木牌子,上面用白色粉笔写着大大的一竖排字:安置下岗工人再就业。
一群人在萧瑟的秋风中排着队,天气有点凉,他们捂紧衣服,一改之前的吵闹,沉默不语。身后是矮小的居民楼,一条斜坡上去,是早已停工的工厂,一片荒草,冰冷的铁门紧锁,在光线下,锁链闪烁着冰冷的光泽。绕过去时,李铁特地看了几眼,发现队列中并没有唐咏的身影。
到菜市场门口,李铁发现还没开闸门,几个中年妇女挑着菜篮子,各自在台阶上坐着,相互之间隔了十来米,互不干扰。她们衣着一概朴素,左顾右盼着,好像在等待着从哪个方向钻出一个人,光顾她们的生意。李铁来到一个系着红色围脖的女人面前,她的鼻尖冻得通红,睫毛僵硬,良久才眨一下眼睛。分明还不到深秋,却如同在经历暮冬一般的寒冷。李铁买了一把芹菜、一个茄子、两个土豆,没有找回零钱。除此之外,他本来想说些什么,但还是沉默地走了。
诊所一般七点开门,所以他还不想这么早回去,于是拎着一袋菜,在街上晃荡。一路人很少,他一直从街头走到街尾,沿着铁轨,经过几栋废弃的居民楼,在一片绿色铁丝网前,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唐咏站在摊位后面,系着一条围兜,用长筷来回挑拨着铁锅里的几根油条。一杯杯豆浆摆在摊位上。尽管戴着口罩,他还是一眼认出了她。
对面那头是一家木料厂,远远望去,空窗上蒙着一层塑料薄膜,门口杂草丛生,几块长条形木板陷在泥土里,墙壁上贴的广告平面画也被撕下来,折角落在地上,没人清理。如果不是车间内传出微弱的机器声响,以及门口的晾衣绳上晾晒着几件滴水的衣服,还以为工厂已经全盘停工了。
这时,从木料厂稀稀落落走出几个工人,他们身着的服装相差无几,走路的姿势大致相同。因为这头的厂房都空了,没什么客源,像是约定好似的,唐咏用报纸包好油条,豆浆用塑料袋装好,半个身子费力钻进绿色铁丝网破了的大洞里,跨过铁轨,一齐交到对面的工人手里,等接过钱后,再从铁轨那头返回来。这太危险了,万一火车到来,来不及走开,后果不堪设想。他想过主动走过去,打个招呼,并提醒点什么,也许她并不会听,因为这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生活。她甚至可能会反问,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即便他再三解释只是偶尔路过,她可能也不会相信,毕竟这里离诊所距离并不短。
他在原地没有挪动一步,只是远远看着她。他和她之间只是医生和患者家属的关系,同时他猜测,也许她自己的家就在附近,那里至少有一个男人在等着她,甚至可能女儿也在。尽管交流不多,但他能够看出,她很珍惜自己的家庭,也很爱自己的女儿和丈夫。他不希望她感到困扰,为一些不必要的事而为难,所以宁可每次只在诊所见到她,一月一次,以一个单纯的医生身份与她交流。天光亮起,如一团揉皱的纸慢慢摊开,显露出蓝色的轮廓,火车的汽笛声依稀传入耳畔。时间差不多了,他摸了摸兜里的钥匙,掉转头,朝诊所的方向走去。
再一次见到唐咏,深秋已过。李铁朝玻璃窗外望去,门口的树木掉光叶子,枝干光秃。
他刚给一个老人做完皮试、不一会儿,老人显露出过敏反应,手臂上出现密密麻麻的红疹。李铁叮嘱老人压好棉签,然后回柜台换另外一种药。
唐咏进来时,并没有催促什么,一如过去,等待李铁忙完。不知是不是药物反应,打完针后,老人的眼皮轻轻合上了,沉沉睡去,鼻孔发出轻微的呼噜声。李铁洗了个手,一身白大褂,来到柜台给唐咏抓药。自天气转凉后,他平日穿白大褂的时候居多,很少脱下。白大褂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眼看去,令人信服,尤其是在患者面前。但从心底来说,他并不想在她的面前穿白大褂。
唐咏安静地坐在位子上,看上去,和以往没什么两样,只是脸色更为苍白些,两个黑眼圈更重了。李铁抓好药,照例是金银花、桔梗、枇杷叶、柴胡,按克称量,用纸包好。他尽量隐藏起自己的情绪,照例问出那句,他最近怎么样了。唐咏的两手揉捏着药包,没说话。李铁心底闪过一丝内疚,换了个话题,说,听说最近社区安置下岗工人再就业,你了解过吗?唐咏摇摇头说,就是填一张表,啥帮助都没有,可能是搞清楚各家情况,担心出什么乱子。李铁说,都已经这样了,还能出什么乱子。唐咏沉默片刻,轻声说,我先前有一个同事,刚查出绝症,为不拖累家里人,当晚就喝农药自杀了。李铁没说话,身子略显僵硬。唐咏低头看着手上的药包,说,但话又说回来,那毕竟是少数,现在厂子都黄了,机器停工了,出来才有出路。李铁闷头“嗯”了一声,说,日子还得向前看,都有各自家庭,都得生活。
温度有点低,他走去把门带上,冷风进不来。座位上的老人闭着眼缓慢地呼吸,白雾在空中聚拢又消散。他本来想买些苹果,最好都是又大又红的苹果,但今日对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戴草帽的环卫工人挥着扫把,清扫落叶。卖水果的吆喝声并没有出现。
李铁回过头,看见唐咏已经起身。他说,这次不等女儿放学再走?唐咏盯着李铁的眼睛,良久,她摇了摇头,说,今天是周末。不知是不是错觉,李铁一时间觉得诊所内的灯泡暗了一些,好像坏了。他避开唐咏的眼睛,手从兜里掏出来,回到柜台后面。他说,在门口等一下,给你个东西。话虽这么说,但他头也不抬开始灌起热水瓶。热水瓶是两千毫升的,他灌得很慢。直到瓶口灌满,热水溢出来时,他才停下。
他在抽屉里取出一个香包,走出门外,唐咏果然没有挪动一步,拨弄着额发,在门口等他。她面对着空落落的街道,环卫工人已经离开了,只剩下一堆聚拢的叶子,几个小孩蹲着围成一个圈,一人持一根树枝干,挑动着树叶堆。李铁说,看你晚上睡得不太好,每晚挂在床前闻一闻,静心安神。他把香包递过去。他没有额外说,这是他花一个通宵做的,在昏暗的台灯下一针针缝制,里面配着艾草、丁香、薄荷、陈皮等。唐咏接过后,放在鼻子前嗅了嗅,一股药香逸散出来。她说,晚上的确休息不太好,容易想得太多,翻来覆去睡不着。李铁说,想什么呢?唐咏小心把香包紧贴着兜收好,看了看李铁的脸,把嘴唇抿紧了。
她掉转过头,这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动作。其实李铁想过再说些什么,哪怕就说一点,但他还是一声不吭,目送着唐咏渐行渐远,一如过往每一个月的此时此刻。斜阳点燃前方的道路,烧成连绵不绝的野火一片,他看着唐咏一步又一步,逐渐消失在视线里。有一件事,其实他一直没有告诉她,每次配药的时候,他都会减少分量,这样药效也会跟着减弱。他在潜意识里希望那个男人的病好得慢一点,这样他见到她的次数也许就能多一点。
夕阳匍匐在地,两侧的门面已经关了:一家是包子铺,蒸笼都收进去了,只留有几块木板在锅炉台上;另一家是五金店,卷帘门拉下一半,大概没开灯,透不出一丝光来。李铁思量着,下一个月该是秋末了,天会更冷,得记得提醒每个前来的病人,多添点衣物才行。他正要掉头回诊所,突然,他的鼻孔嗅到一丝奇怪的气味,耳边传来噼里啪啦的爆裂声,他稍一撇头,注意到落叶堆上逸出一缕缕黑烟,原来是对面那群孩子划燃火柴,把那堆干燥的落叶引燃了。
四
过往的病人一个个痊愈,新的病人一个个涌入。李铁每天要接待各式各样的人,但在闲暇,他会时不时把头瞥向窗外,想着也许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就能看到唐咏从诊所门口经过,哪怕她并不进来。但一个月过去,他始终没有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
秋天步入尾声,唐咏依旧没有出现,李铁努力压制住心底的不安,不断劝说自己,也许她一时忘记了,或者忙着照顾家里,抽不出时间来。他在给其他病人打针时,好几次找错血管位置,以前他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一个病人是小孩,被针连扎几次,哇哇大哭,家长在一旁发起脾气,直到几个与李铁关系好的病人一阵好说歹说,才劝住。后来两人走了,李铁没有收他们的钱。
又是几个月过去,一直到第二年春天。
某天,李铁刚从玻璃柜台后面,取出一盒阿司匹林交到一个中年妇女手上,这时,他看见门外出现一个自己略感熟悉的身影。他们仅有一面之缘,是唐咏的丈夫,李铁记得,他叫邹正海。
邹正海看上去好像比以往壮了一点,背也不驼了,面色红润,和唐咏说的那个病卧在床、不停咳嗽的虚弱形象截然不同。
李铁虽然感到有些诧异,但还是走上前去,和他握了握手。李铁去接了两杯水,两个男人坐在椅子上。李铁说,好久没见了。邹正海说,是啊,一年多了。李铁说,看起来恢复得不错。邹正海“嗯”了一声,说多亏了你。李铁换了个话题,说,就你一个人来啊,她人呢?邹正海摇摇头说,别提了,年前就出了事,在铁轨边上,来不及跑。他从兜里抽出一支烟,咬在嘴里,含混不清地说,人当场就走了,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就那么一瞬间,李铁感到手中的杯子很冷,那是彻骨的寒,但他久久没有放下,好似宁可让这种冰冷从手指渗入血肉,沿着血管直抵心脏,将自我彻底冻结。他的身子摇晃了一下,起身关掉电视机,很想让自己独自待一会儿,但邹正海仍喋喋不休,丝毫没有注意到他的异样。李铁只好说,那你也挺不容易,自己病刚好,又需要一阵忙活。邹正海的声音顿时止住了,看向他,眼神略有奇怪。他说,我的病,在夏天就差不多好了,还是多亏了你开的药方。水杯掉在地上,李铁重新捡起来时,水已经淌了一地。一时间,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脑子里浮现出那个在秋天按时出现的身影。
这时,一个小女孩走进来,杏仁眼、弯月眉、嘴唇紧抿,正是邹正海的女儿。她的个子比李铁去年见到时长高了一些,头发也变长了,系着一个红色蝴蝶结。她在邹正海旁边坐下,两手紧贴双腿,抚平裙褶,一副十分安静的模样。与此同时,李铁注意到,她的胸前挂着一个绣着花纹的药香包。小女孩说,爸,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家吧。邹正海别过脸说,我来给李医生说句谢谢,没他,我的病也不会好,你也说一声吧。小女孩并没有回答,跳下来,径直朝门口走去。邹正海略带歉意,对李铁说,不好意思啊,都是年前那事,给孩子闹的,不爱说话。随后他又呵斥一声,要小女孩重新回来坐好。小女孩并未坐上去,而是站在一边,她咀嚼着什么东西,瞄准垃圾桶方向,从嘴里吐出一块口香糖,口香糖落在垃圾桶旁边。邹正海用手指了指女儿的后腰,说,她之前一直寄宿在学校,基本不回家,缺家里管教,别介意。李铁定定地看着小女孩的侧脸,好半天才回过神,然后摇了摇头,说,没什么。他走到抽屉前,翻出一根棒棒糖,递给小女孩。小女孩撕开糖纸,含在嘴里,礼貌地说了一声,谢谢。
李铁说,你每天过来,我每天给你一根。小女孩的眼睛一下亮了,但话语里带着犹豫,她说,真的吗?李铁点点头,说,不需要进来,只要每天放学路过,在玻璃门前敲一敲就好。小女孩好像有些惋惜,说,我一个月才回来一次,马上要放暑假,再见面,只能是秋天了。李铁说,没关系,那咱们秋天见。小女孩把眼睛偷偷瞟向她的父亲,但邹正海没有反对。
李铁蹲下身,理了理小女孩脖子上的药包,因为绳子松了,他重新系了一下,紧接着,一股熟悉的药香钻进他的鼻孔。黄昏时候,他一直送邹正海父女到门口。临走前,小女孩还在向他挥手。下一次见面,应该是一个新的秋天,瑟瑟秋风摇动枯枝,没有掉下的枫叶,像火星一样灼亮天空。
李铁心想,下一次见到小女孩时,也许她会长得更高,而他也会苍老一些。当他每一次看到小女孩的脸庞,就会不自觉想起唐咏,就好像她还活着一样。一次又一次。

罗志远,1999年生,湖南长沙人,本科毕业于西南大学文学院,现为西北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在读硕士,作品散见于《作家》《天涯》《西湖》《湖南文学》等。有小说被《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已出版小说集《书法家》。
来源:《芙蓉》
作者:罗志远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