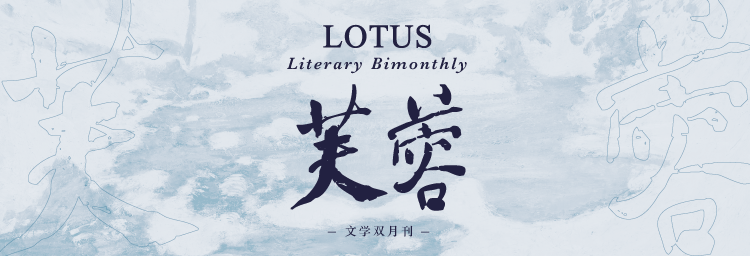

海棠之吻
文/许冬林
一
记得那是一个南方的秋天,没有云,天空蓝得清透明白。
来找我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三十七八岁的样子。她坐在我对面,说话语调温柔,但温柔的言语里又影影绰绰藏着凋零。她来,为的是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名叫海棠,是我的学生。
我第一回在课堂上叫海棠这个名字时,心想,为之取名的一定是女孩的母亲。海棠花美,而“海棠”两个字发音时,舌尖处似有微风和阳光的清甜和明亮。一个女人,新做了母亲,她内心甜蜜,此后的时光因为一个新生命的到来而充盈饱满。她对女儿也许不设定太宏大的人生目标,是只做一朵海棠就好。
海棠的母亲坐在我对面,说着说着,泪终于憋不住。她恳求我帮忙,喊来她的女儿。她想见女儿一面。
他们是夫妻离婚,海棠判给了父亲。我跑到教室,找到海棠。海棠很懂事,每次见我,老远就跟我招呼。可是这一回,当我说到她母亲坐在我家等她时,海棠竟退回座位处不肯出来。我拉着她的手,贴在她耳边悄悄说:“小傻瓜,天下的妈妈都是最爱自己的孩子的。你看,妈妈这么远过来,就是想看看你。你无论如何得去跟妈妈见一面,让妈妈看看你。你还可以跟妈妈说点你的学习情况……”
不知道是出于礼貌,还是被我说动,海棠最后同意去我家。她低头走在我身后,一路沉默,沉默得像一枚不肯发芽的果核。
将海棠引到她母亲面前后,我即离开,站在楼下等,好让这一对母女贴心贴肺地说说话。可是,才不到十分钟的样子,海棠就下了楼,边走边小跑着往教室方向去。我正要拉她,想留她和她母亲多待会儿,可是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已经斜着膀子从我身边风似的掠过去了。她是低着头跑掉的,脸上有泪水。
我心里一叹,慢慢上楼。坐在桌边的,是那个看起来比刚来时更加萧索更加孤单的母亲。
海棠的母亲一边抽泣一边擦泪,过了好一会儿才艰难平复情绪,慢慢跟我说起一些事。她和海棠爸爸离婚后,就回到一百里之外的娘家那边另组了家庭,海棠的爸爸在外做生意也另娶了一个贵州女子回来。海棠母亲因为听说这位贵州女子打算过年回娘家带上海棠一道,所以格外不放心,生怕人家会将自己的女儿拐去卖掉,此番来学校,既为见女儿以慰思念之苦,也为叮嘱女儿千万别跟后妈去人生地不熟的异地。但是,海棠却不认同她母亲的意见。
我后来想,这一对母女的短暂相见和不欢而散,根由大约不在去不去贵州这件事上。而是,这个算是某种程度上“失去”女儿的母亲拼命伸手想要揽回女儿,而女儿已经倔强地不肯回头倒向母亲的怀中。因为在海棠心里,她似乎已经更爱她的那位来自贵州的后妈了。
因为这件事,此后我便对海棠更多一些关注,我也像她母亲一样唯恐她后妈对她不好。海棠的长相在班上女生中并不算出众,但是她长长的辫子每天都梳得特别仔细,一点不乱,一看就是有大人帮忙梳的。大约是她后妈梳的。海棠告诉我,是自己的亲妈找爸爸离婚的,大约是怪爸爸挣钱少。关于这个,我听海棠妈妈说过,她说海棠爸爸做生意总是不挣钱,她到娘家到处借钱给她爸爸,可她爸爸总是不争气。海棠的妈妈大约对她爸爸失望透顶,终于提出离婚,可是放心不下女儿。海棠对她母亲有抱怨,所以平时不大肯见她母亲,她觉得妈妈不爱爸爸,便也是不爱她了。
后来的一次家长会上,我见到海棠的后妈。她很安静地听我说话,很小心地问我海棠在学校的情况。我后来也听海棠说起她后妈每天晚上陪她学习的事,心里也挺感动的。但是,我又始终希望海棠和她亲妈的关系能有改善。
冬天的时候,我收到一个泡脚桶,是海棠的亲妈从我同事那里打听到我的联系方式,网上买来寄给我的。我一时不好退回,便收了,将泡脚桶送给了我母亲用。我心想,也许是她们母女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善,这个小母亲心里高兴,所以感谢我的帮忙。
翌年的一个海棠花开的季节,海棠的亲妈又来了,我热情接待了她,坐下一聊,我才知道这个母亲已经又有小半年没见到女儿了。女儿似乎铁了心不肯见她,她所有的方法用尽,想来女儿是最听老师话的,所以只得再从我这里求助。
这一回,我又到教室,悄悄贴在海棠耳边说她母亲来了。海棠礼貌地对我笑笑,然后一个劲地摇头表示不去见。她说,她怕见了自己母亲,让后妈知道了,后妈会伤心。她还说,后妈因为她,都放弃去生自己的孩子。她说到后妈时,眼泪儿一串串挂出来,挂满小小的微黑微红的圆脸蛋儿。她那伴着哽咽的微微沙哑的声音里,净是对后妈的爱护和疼惜。我心想,小傻瓜,哪有女人为了继女放弃去做母亲,或许是后妈自己生不了孩子呢。但是,我也只是心里想想而已,我没有把自己这样一个来自成年人的阴暗的揣测告诉海棠。再说,即使是一个生不了孩子的女人,她能把继女视如己出,也令人尊敬。
那一天,我没能说动海棠。我一个人走回家,面对一个焦急等待的母亲,深感抱歉。
她告诉我,她想孩子实在想得难受,想得整夜不眠,抱着丈夫哭。
她把我的眼泪也说下来了,我劝她再生一个,或许多少可以缓解这无止境的思念之痛。她说他们是有这计划,但是如今年纪已大,不是想要就有的。
在那个花气蓬勃的春天,我送一个见女未着、失魂落魄的母亲出校门。我们路过校园那几棵正开花的树边,她脚步放慢。校园水泥路边那几棵海棠树上,浅粉色的花朵开得好似半天云雾从枝丛里弥漫出来,那云雾在阳光下随风变幻,仿佛又变幻成小女孩粉红的笑颜。我指指,轻轻对她说,那是海棠。她微微点头,抿了抿落到嘴角的泪珠,对我感激似的笑笑。
二
北京的鲁迅文学院里,也有几株海棠,叮叮当当地结了满树的果子。我9月刚到时,那海棠果还是青的,猜想那味儿一定极酸。转眼两个月过去,那满树海棠果已是张灯结彩的红。我好奇摘一颗品咂,酸里已透一些甜来。
我和同学常常在这秋天的海棠树下散步,一边沐着树间漏下的日光,一边闻着若有若无的果香。一日,同学红蕾跟我说起我给她的印象。她说我初看是阳光的,是欢喜的,但再走近就不容易了,因为我身上似乎藏有一点冷和疏离。我后来细想,觉得她说的话是有几分道理,我确实是害怕和别人太近。
我看着树上的海棠果,忽想起十多年前我的那个名叫海棠的女学生,想起她和她母亲的眼泪。
最后,我想起了我和我的母亲。
我是从哪一天起,就抱着一块冰在怀里,一个人悄悄走远,害怕和别人太近呢?
我想起母亲如今常常责怪我,结婚后从不肯在娘家待上一夜,其实她是责怪我不肯落下脚、陪她一夜。
她不知,即使是母亲,我也害怕和她贴近。
成年后,我几乎不曾和母亲同床而眠过。每次回娘家,即便再晚,我都要走。母亲怕我嫌弃她的床不够干净,总是解释说特意为迎接我而刚刚换过被子,而我则解释说晚上要回家用电脑做事情。
母亲不解道:“难道有那么多文章要写?”
我一边笑着一边撤退,顺手带上母亲的门。我终究要走。
文章是写不完的。可是,我到底为什么不留下来陪母亲睡一夜,总是让她失望呢?
每一次离开母亲家,我都会感到愧疚。可是如果让我退回门口,我还是选择要走。
因为,跟母亲同睡一床,在我这里,那是陌生的。是的,我和母亲睡在一起,我觉得像是跟陌生人睡在一起。我会不敢伸脚,不敢放肆展开四肢。我更害怕,会一不小心碰到母亲的肌肤。
我想起童年时,在我们家那个临河而居的老宅里,母亲抱着弟弟坐在堂屋里逗弟弟开心,我不远不近默默站在旁边。母亲每逗笑一次弟弟,总要脸贴到弟弟脸边,啪——很响亮地亲一口弟弟。我就站在母亲身边,不远不近。母亲不曾转过身亲过我一次。
常常是那样的夏日,弟弟衣服穿得少少的,母亲抱着弟弟坐在堂屋里,坐在穿堂风里,她身子一俯一仰,以巨大的幅度抱着弟弟起伏。他们在穿堂风里用身子的俯仰起伏把小小的椅子坐成了秋千一般。母亲常常一边逗弟弟,一边幸福甜蜜地抒情:“我的心呀——我的肉呀——”
母亲抒情完毕,又会补上响亮的一吻。弟弟简直成了母亲的无上美味。我就站在母亲身边,不远不近。河水映着天光斜斜照进屋子里,到处都是明亮的,我也站在明亮的光照里,可是母亲似乎不曾看见我。我形若虚无。我不远不近,默默看着母亲一口又一口亲着弟弟。一口都不会落到我脸上来。
午后的风贴着河水吹拂,然后穿过柳树和榆树的枝叶,再穿过我们的堂屋。风把柳枝儿和榆树枝儿吹得软软的,把弟弟和母亲吹得像是起了毛,他们的笑声有谷类发酵的甜香。风把我吹得凉凉的,我要凝结了。
我凉凉的,默默看着母亲亲着弟弟。一口都不会落到我脸上来。
一口都不会落到我脸上来,我好像也没有恨意。我只有一点失落,一点当时还不能懂得其中含义的伤心。我看着母亲亲弟弟,像看着隔壁婶婶亲着堂弟一样,只是羡慕那亲吻大约像刚出锅的米饭一样冒着芳香的白气,它烙在弟弟脸上,软糯而微烫吧。我没有恨意——谁会恨一个邻居亲吻她的孩子而不亲吻自己呢。
最令人浮想的是晚上,特别是冬天的晚上。那时,母亲一边给弟弟脱衣服,一边亲弟弟。亲过,母亲睡下,将弟弟揽在怀里。弟弟像种子睡在瓜瓤里一样,睡在母亲雪花膏香气弥散的怀里。我就在对面的床上,自己静静地脱衣,然后睡在父亲身边。我抱着双臂在冰冷的被子里,不敢靠近父亲。我弯着我的左臂,弯到身子右侧;我弯着我的右臂,弯到身子左侧。我枷锁似的自己抱紧自己,用自己的体温,慢慢焐热身上的被子。我将被子掖到耳边,依然能听见母亲啪的一声亲弟弟的声音,那宣告要关灯了,一天隆重结束,夜晚正式开始。在一日的终了之时,父亲不会亲我,母亲更不会。我沉入黑暗中,像一个没有晚餐的孩子,可是也乖乖地睡觉。
我期待节日。
一到节日,我便会去外婆家。七岁那年入学读书,七岁那年的另一壮举,便是我可以独自去外婆家了。我一个人翻过高耸的江堤,穿过足有一里长的坟地,穿过狗吠相迎相送的村庄和大得没边的田野,到达七八里之外的外婆家。外婆家在长江边的一个沙洲上,那时,每到假日,小姨便会早早站在屋子西边的木槿篱笆边等我。
我远远看见平坦开阔的沙地中间立着一座并不高大的土墙房子,那是外婆家。它像江面上一只正泊岸的船,而站在木槿篱笆边翘首等我的小姨,像是船顶上一面迎风招展的庄严的旗子。
我奔向小姨。小姨牵着我的手,或者将我高高抱起。肌肤相贴的那刻,我像是一块就要摇摇欲坠的石头,忽然稳稳从悬崖边坐回来,躺倒在一块温厚可亲的大陆上。
我迎向小姨,其实是迎向一个母亲。
我其实在懵懂之年,已经不要生我的母亲了。我认小姨为母,从小姨怀里出发,把蒙古长调一样低沉悠扬的爱和惦念都给了小姨。
(节选自2024年第3期《芙蓉》许冬林的散文《海棠之吻》)

许冬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联招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创作方向)在读硕士。散文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散文》等刊物。著有散文集《外婆的石板洲》等十余部。
来源:《芙蓉》
作者:许冬林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