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蝉 月色与道
——论李勇诗中意象的哲思建构
文/舒常敏
清代刘熙载于《艺概》开篇明义:“艺者,道之形也”,揭示艺术与“道”的内在关联。这一理念既承接儒家“文以载道”的传统,亦融汇道家“大道至简、道法自然”的思辨,强调艺术应超越技术层面,体现对宇宙与人生的哲思。
陆机曾谓:“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李勇诗中的“言”,乃文学之言说;“存形”亦非视觉直观之画,而是邀读者共同建构的意象之画。《今夜,我枕着月色入眠》中夜的孤寂、路的模糊、星的疏朗、灯的阑珊、花径的幽香、秋蝉的嘶哑、月色的苍凉,无一不是诗人所铺设的意象线索,待读者以独特的审美与辩证的哲思,完成最终的意境还原。
《秋蝉》与《今夜,我枕着月色入眠》在创作上颇具互文之妙。两者皆以秋声、月色为底色,以蝉鸣为情绪转折的突破口,勾勒出生命深处的苍茫与孤独。诗人行走在异乡的夜里,听见草虫嘶哑、看见灯火如谎,一切景语遂成情语,外在物象纷纷向内转化,成为心绪的投影。
李勇的诗,形神兼美。其“形”可见可感,语言清丽、意象纷披;其“神”则隐于意象叠加与情绪节奏中,需反复沉吟方可领会。例如“枕着月色入眠”非爱情诗句,而是诗人在蝉声与秋意中获得顿悟后心灵安宁的一剂良药。秋蝉在此不仅是季节符号,更是生命终局的象征。诗人借蝉之将死,乃仍要嘶鸣,表达对生命尊严的认可:即使注定逝去,也要发声、也要永存、也要绽放。
诗中所言“没有爱情/没有玫瑰的芬芳”,并非吐露情殇,而是对生命进程中某些失落“情趣”的叹惋,进而转向更广阔的生命观照。诗人从一己之寂寞,跃入万物之苍茫,体现出中国古典诗学中“由小我入大我”的崇高追求。
《秋蝉》中,“残荷、断桥、山寒、水瘦、寒露”,一系列疏冷意象的堆叠,与“远去的苍茫”形成呼应,构建出天地萧瑟、岁月无情的整体意境。而秋蝉生命之短暂、其临终仍竭力鸣叫的姿态,又被赋予悲壮与神圣的色彩——生命虽微,其声亦贵。
李勇将古典诗词中经典的秋蝉意象引入现代诗语境,不仅延续了传统意象的抒情功能,更注入了现代人对生命、孤独、死亡的深层思考。在两首诗的背后,可见一个步入人生秋季的诗人,如何以诗为证,对抗遗忘、审视存在,并在艺术中寻求超越性的价值。
道为艺之本,艺为道之显。李勇的诗,语言清净而意境深远,其所构建的视觉与心灵之“画”,不仅令人沉浸其间,更指引我们走向对生命本质的沉思。每读一遍,都可抵达一番新的境界──“根极于道”与“道法自然”;每听秋蝉,亦或可见那疏星之上,思绪仍在不停地舞蹈──悲凉情感与高洁品格的双重意向。总之,李勇的诗可以照见一个人的心性,诗如其人,沉稳而内敛,不显山露水而自悟“终极真理”。
附:
今夜 我枕着月色入眠(外一首)
作者丨李勇
一个人的夜晚
可以信马由缰
无需酝酿太多的故事
我用脚步丈量内心的彷徨
路是模糊的影子
思绪在疏星之上舞蹈
远处灯火阑珊
我看见谎言在暗处游荡
一声草虫的嘶哑
颤落一片忧伤
路旁的花径
在苍茫辽阔中迷离
有一种残香的魅惑
将寂寞缠绕
今夜 我行走在回望的路上
黑夜吞噬了远方的森林
今夜 我迷途在异乡
没有爱情
没有玫瑰的芬芳
彳亍在秋蝉的浅吟里
今夜 我枕着月色入眠
秋蝉
不动声色
你蛰伏在季节深处
偶或地嘶鸣
洇湿秋的离歌
秋风萧瑟
你啃噬最后一片月色
在无垠的暗夜
独自忧伤
残荷断桥
山寒水瘦
载不动岁月的一阙愁肠
一滴寒露落在掌心
在低处聆听
你禅意的背后
注定是一片远去的苍茫

舒常敏,女,岳阳县月田镇小学教师,湖南毛泽东文学院岳阳作协首期作家改稿班学员,岳阳市作协会员。作品见《中华散曲》《湖南诗词》《岳阳文学》等。

李勇,笔名麦果,湖南邵东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湖南省临湘市作协党支部书记。先后在《诗刊》《北京文学》《中国青年》《解放军文艺》《湖南文学》《中国文化报》《长江丛刊》《特区文学》《延河》《芒种》《诗歌月刊》等上百种刊物发表文学作品800余件,曾获全国诗赛二、三等奖及第五届岳阳文学艺术奖,作品入选30余种选本,出版有诗歌集《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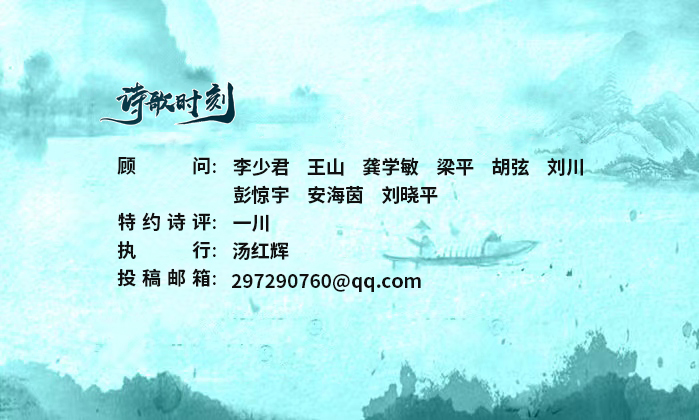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舒常敏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化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