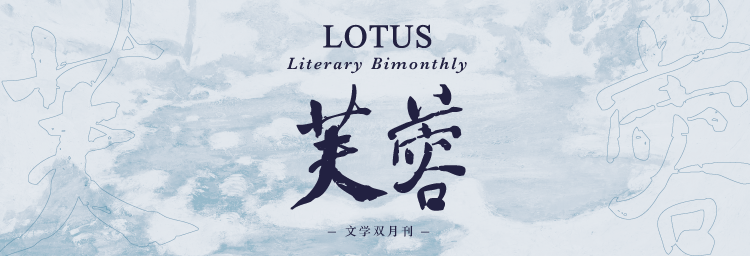

神泉水(短篇小说)
文/王啸峰
从内心讲,我不愿意回故乡。
母亲催了好几次。想到可能是她最后的心愿,我请了两天假,坐高铁回了河阴市。
市中心街坊改造时,把街巷改成商业区,家里老房子被拆。我把母亲接过来住。河阴郊区的补偿房,我只去过一次。
我住了宾馆。去了老字号馄饨店吃午饭。店里除了收银的,吃客、服务员全说普通话。我感觉自己像个游客在景区里。还好,馄饨味道与儿时记忆差不多。
馄饨店出来,我约的快车到了。
城市即使再变,我也能认出底色。可市郊一条条高架和隧道,我完全失去概念。直到车进入墓区前的山村,我才认出,这是每年清明节要来的地方。
墓区管理员很客气,表示理解老太太心情。她从抽屉里拿出价目表。
父亲去世早,是这里第一批落葬者之一。当时都是一块碑、一个墓穴。
我请她带着去看不同价位的双穴墓地位置。
路过父亲所在墓地时,我停下脚步。山脚下的这片墓地,早被一棵棵柏树包围起来。有风过来,柏树林齐刷刷地微微颤动。
果然,最高价位的在东南坡中间。阳光充沛,视野开阔。远处湖光山色一览无余。最低价位的在刚开出来的平地上。中间价位的在山坳里。
我选了东南坡正中间靠过道的位置,请管理员先去办手续、开票。
下山,我走进柏树林。半年时间,父亲墓上又落了很多柏树针叶。我鞠了三个躬,掸去柏树叶,抚摸着一左一右两棵柏树。
我感谢它们对父亲的忠诚陪伴。我第一次看见它们的时候,还是小圆柏苗。母亲拉我走,我不肯。有亲戚把我抱起来,我双脚离地,试图抓住树枝。
他们不知道,我在等小黑。他答应过我会来。
唐山大地震后,河阴市民疯传也要大震的谣言。体育场铁丝网门被推倒。早去的人家占领了足球场。
父亲带我进体育场时,跑道上已摆满竹床、竹榻和藤椅。我们在跑道边上铺了一张草席。我还机智地带了个小枕头。头靠枕头,眼望星空。
好多人在议论不寻常的天象,火烧云、月晕什么的,我听不太懂,只觉得比闷在老房子里强多了。
突然,天边闪过几道强光。
“地震啦!”有人惊呼。
随即,整个体育场闹哄哄。
众人搬着椅凳往外跑。
我有点纳闷,不是为了躲地震才到这里来的吗?
父亲也卷席,叫我快回家。
一场雷暴雨把我们落在半路。
百货商店台阶上,站着不少从体育场跑出来的人。
人在躲雨,竹椅、藤椅在淋雨。雨大风大的时候,我想起父亲讲的东海龙王的故事。龙王一张口,风雨就一阵紧似一阵,还带来雷公和电母。
闪电和雷声远去,雨渐渐停了。
父亲扛着席子快步走在前面。
席上有水滴到我头顶,我追着父亲问:“我们还去体育场吗?”
拐进弄堂,父亲刚推开家门,又退回一步,望着弄堂深处,对我说:“弄堂底有亮光呢。”
弄堂到底转九十度弯,迎面撞上杨老师家。我站回弄堂当中,踮脚张望。那光闪烁不定。位置似乎在九十度弯角上,我们平时玩耍的小黑屋。
父亲把席子交给母亲,打水去天井里冲澡。母亲上了门闩,让我也去洗。
我借口屋里太热,要睡客堂竹床。母亲给我一把扇子、一条大毛巾。
“肚子千万不能着凉。”她打着哈欠说。
我怕竹床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根本没上去。
我坐在门槛上,蝉鸣声传来,过几天,蟋蟀也该有了吧。
等得差不多,我又看了一眼夜空,星星开始眨眼,我该行动了。
我悄悄地把门闩移开。
杨老师与父亲是同事。她教语文,父亲教数学。
虽然父亲没有在家议论过她,但是大家都觉得她挺怪。
她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弄堂底的平房里。围墙很高,宽板大门黑漆,开一个邮件投递缝。
我们的比赛通常是这样的,从弄堂口往里跑,碰到那扇黑漆门后返回,谁第一个回弄堂口算赢。
无论我们碰多少次黑漆门,杨老师也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出来训斥。里面一直平静得像池塘。
她带着两个女儿一起去学校,傍晚回来,在弄堂里碰到人,微微点头致意。
我们想了想,除弄堂外其他场合,从来没有她们的身影。她们的吃喝拉撒,成为我们探秘的重要内容。
我拉住倒马桶的阿婆问,她耳聋背驼,一个劲说:“铜钱给得多的,多的。”
我爬上自家围墙,目光越过屋脊眺望杨老师家,除了黑黑的屋脊,什么都看不到。
我趴在投递缝上张望,只看见晾衣架和飘荡白色裙子的一角。再去看时,里面挡了块黑布。
弄堂里几个路灯坏了。弹石路面坑坑洼洼,我避开水坑往里走。拖鞋噗叽噗叽,声音怪异。我把拖鞋拿在手上,像握两块砖头。
小黑屋映出来的光时明时暗。传说中弄堂鬼火就像这样。
我放下拖鞋,摸了几块石子在手里。
紧靠着杨老师家边上的小黑屋,不知道是谁家的。我从记事起,就荒废着。门窗早就被人取走派上用场。哪家捉漏,就爬上小黑屋拿几块望砖、几爿瓦。
小黑屋快被掀掉顶时,街道要做仓库,简单整修了。仓库里东西被领完了,小黑屋被我们占领。
我通过没有玻璃的窗户朝里看。火盆里稻草在燃烧,草是湿的,烟很大。烟雾中,辨得清靠墙横着一张板床,一个人躺在席上。
风刮过来,我忍不住咳嗽。
那人一跃而起,连声问:“谁?谁啊?是谁?”
声音奇怪,像公鸭嗓音。
我和那人并排坐在板床上。他递给我一片烤鱼干。
“我刚烤的鲫鱼。”
“稻草赶蚊子,还能烤东西啊。”我侧脸看他,全身黝黑,眼睛细长,嘴扁宽大,还往下弯。
我估摸着他起码大我五岁,从口音判断,像湖区一带人。
他烤的鱼,可以用手掰下来吃。香味夹杂着烟熏味一起进入我口鼻,又香又刺激。
见我吃得开心,他从钓鱼说起,什么鱼用什么饵。鱼怎么处理不腥。蒸鱼、氽鱼、烤鱼、红烧鱼等各种方法的要领。
我嚼完最后一小块鱼干。
“你从哪里来?躺在这里干什么?”有几次,我碰到过乞丐在小黑屋过夜,却不是这个架势。除了板床,还搬进来一只小方桌、两条板凳、一个衣橱。
“我爸爸、妈妈都死了。”他转头盯着我看,我被他看得低下了头,“大队里把我送到姑姑这里。”
“谁是你姑姑?”我站起身,一脚踩在燃烧的稻草堆边,几颗火星跳出来。
他缓缓伸手指了指杨老师家。
“杨老师?她不让你进门?”我握紧拳头,挨个在床、橱、桌、凳上胡乱敲打。
他走到屋脚,拿一把稻草扔到火盆里。
稻草特别潮,一下子,我眼泪流出来。
蒙眬中,门口出现一个高大身影。
我擦把泪扑上去,高声叫了声:“爸爸。”
父亲让我把拖鞋穿好,问了他几个问题。
“好吧,有事尽管找我们。进弄堂左手第一家。”父亲拍拍他肩膀。
出门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都有绰号,我叫‘姜块’,你就叫‘小黑’吧?”
他点头,嘴角往上努力翘。
父亲在放暑假。吃好早饭,他对我招招手。
我们走到弄堂底。
小黑在修门。他试着用废铅丝穿过锁孔,固定门和门框。
父亲走进屋内,看看窗,摸摸家具,望望屋顶。转身走出去。我要跟着他,他让我帮着小黑先搞卫生。
碎石、小砖块、垃圾,我俩用簸箕装,倒在火盆里,往街上垃圾箱运了好几次。
路过我家时,我瞥见父亲、母亲都在忙碌。
“那是你妈吧?”小黑问得很轻。
我回答很响亮。
“你没有兄弟姐妹?”小黑惊讶地再问。
“没有啊。你呢?”我想想街上好几个伙伴都是独子。
“我有四个姐姐。”小黑伸出手,弯曲小拇指,做出奇怪手势。
收起手指,他声音放大:“不过呢,她们都不要我。在我们农村,她们都得听婆家的,做不了主。”
我突然想到那些女同学,才二年级,就已经很蛮横。如果在乡下,她们一定会被好好收拾。
我笑出声来。小黑认为我在笑他,补了几句:“也有女的‘狠角色’,我们隔壁小队长就是个女的。说起话来,嗓门比男人还粗。干起活来,两个男人都扛不起她肩头担子。”
父亲爬上屋顶,整理砖瓦。
母亲嫌我俩打扫得不干净,吊了井水,拖了水泥地,擦了家具。她给小黑两盒蚊香,不让他再烧稻草。
父亲去街上喊来划玻璃的、锁匠、木匠、电工。
一帮人忙了半天。午饭时,小黑屋亮堂干净了。
小黑穿上灰汗衫到我家吃饭。
黑漆大门始终关得紧腾腾。
母亲看了看闹钟,三口两口把饭吃完。
“我去上班了。饭菜全部吃光啊!这种天,到晚上全要馊的。”
纺织厂离我家很近,大街往南第一个路口朝东拐过去两三百米就到。母亲是班长,又是先进生产者,总是提前半小时去。
中班要上到晚上十点,她没在十点半前到过家。
我最不情愿她上夜班,白天总盯着我。不论到哪里,心里都发慌,随时随地身后都会传来她的吆喝声。
父亲正相反。他笑着给小黑夹菜,问他今后打算。
“我没什么打算,我听姑姑的。”小黑米饭吃到第三碗。
“对的,对的。应该听杨老师的。”父亲吃完饭,喜欢点根烟。几口烟下去,他咳嗽起来。最近他咳得厉害。母亲不在,他才敢抽。
说起杨老师,我气上来了:“她们太过分了,像乞丐一样对小黑。”
父亲拍了拍我的头:“不能这样说。杨老师也难。”
小黑停下筷子,小眼睛眯着,目光里透出对父亲的信赖。
父亲让我俩下午买米、拷酱油、打菜油、搬煤球。
“做完,你们可以去游泳。”
我兴奋地跳起来。那时,我刚会“闷头游”,游泳正在兴头上。
不知道是不是父亲算好,还是巧合,他给我的粮票全用完,钱却多一分钱。
我做主,买了两颗咸味硬糖。
小黑“咔嚓、咔嚓”两三下就把糖嚼下去。我教他得到既咸又甜滋味的技巧,他后悔地蹲在地上挠头。
我们借煤球店里的小板车,一个推,一个扶。推要稳,扶要把好方向。小黑又赤了膊,胸前、胳膊上鼓起一块块肌肉,汗水在上面流淌,亮亮的。我看看自己白白、细细的胳膊,叹了口气。
去游泳的路上,碰到几个伙伴,我把小黑介绍给他们。
他们让我们跟着一起去工人文化宫游泳池玩。
小黑步子慢下来,越来越慢。后来,干脆弯腰捂肚子不走了。
等伙伴们走远了,他蹦跳着往反方向跑。
“你假装肚子痛,想干什么呢?”我气喘吁吁地跟着他。
“游泳池想想都不是玩水的地方,我们到河里游。”他做了快走的手势。
野泳!我心跳加速。平日里听大人们说到运河里吊船出去十几里,再吊船回来,既羡慕又害怕。
父亲警告我,野泳危险,吊船更是拿性命开玩笑。他说有个自认为水性好的,吊船时大意,脚伸到螺旋桨里,一下子毙了命。
见我脚步犹豫。小黑问我一个问题:“知道我叫什么吗?”
我昨晚似乎问过,但是起了绰号,忘了大名。
他双手同时斜伸向天空,做了划水动作。“我是‘浪里白条’啊!”
“吹牛!”我瞪了他一眼,准备转身跟上伙伴脚步。
“好了,好了,我叫张阿顺。”他站定了,大声对我说。
“那你就是‘浪里啊白条’!”
我俩齐声大笑,夕阳光在我们身上抖动着。
我知道运河边上有个大水塘,街上好多人在那里洗澡、玩水。
水塘四周环绕着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水碧绿深邃。
小黑见到水,像鱼一样扎进去。
一个猛子,好久没冒头。岸边的人停下正在拧毛巾的手,紧张地商量要不要下水看看。游泳的人也扑向深水探寻。
我想自己犯了大错,焦急地跺起脚。
突然,水塘中央泛起几朵大水花,一条黑影高高跃出水面。
“小黑!”我禁不住大声吆喝。
我小心地下水,水塘有缓坡,脚碰到砂石,有的滑滑的,有的尖尖的。
小黑扶我进深水区,脚突然腾空,踩不到东西,我牢牢抓住他胳膊,不敢放手。
他回头,指着岸边问我:“那是谁?”
我回头一分神,他甩开我的手,往前游去。
我一惊,身子往下沉,内心恐慌,喝了几口水,手划脚蹬,头冒出来,又沉下去。一个可怕的念头袭来:我完了。小黑!你在哪里?可我既看不见他,又喊不出救命。只能靠自己了!
我努力保持手脚协调和节奏。打水、夹水、踢水。突然,我发现自己的头能保持在水面上了。我望见小黑了,他正仰面躺在水里,伸出手招呼我划过去。
他的手带着水珠,在落日余晖下,闪着亮光。

王啸峰,男,1969年12月出生,苏州市人。现为中国电力作协副主席、江苏省电力作协主席。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钟山》《花城》《作家》《芙蓉》《上海文学》《青年文学》《散文》《美文》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作品多篇。出版有散文集《苏州烟雨》《吴门梦忆》《不忆苏州》、小说集《隐秘花园》《浮生流年》等。作品入选年度最佳小说集、散文集,被选入《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小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好小说榜单、城市文学排行榜,曾获第六届和第七届紫金山文学奖、第三届钟山文学奖等。
来源:《芙蓉》
作者:王啸峰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