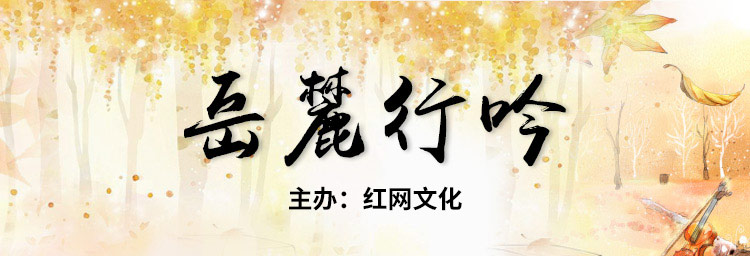

借母溪。彭福林/摄
感悟借母溪
文/李骥
车辙碾过乌宿大桥的青石板时,山风裹着松针的清苦与野蔷薇的甜香漫进车窗。这是我第三次来沅陵。前两次总被“借母溪”这个名字绊住脚步——“借”字太轻,像借半卷旧书、讨一盏清茶,可当我第三次站在溪畔,风里忽然浮起阿婆洗衣的棒槌声、石臼里糍粑的闷响,还有山民灶屋里飘来的腊肉焦香,才惊觉这“借”字原是天地设下的谜面:我们借的哪里是山水?分明是时光里未褪色的活法,是烟火褶皱里未被俗世玷污的“归处”密码。
远处溪涧的“叮咚”与山风里松针的“沙沙”应和成一曲自然的歌谣。我忽然懂了,这方山水的“故事”从不在典籍里,而在苔藓的褶皱里——是松萝垂落时抖落的晨露,是溪石被水磨圆的棱角,是阿婆洗衣时棒槌与青石板的私语。它们沉默地生长、流动、交织,用最原始的生命逻辑诉说:所谓“永恒”,不过是万物各安其位的默契——是“我活,你亦活”的朴素共生。
无人机升上半空时,绵延的森林在武陵山脉的褶皱里舒展腰肢。深绿的乔木如巨伞,松针上的露珠折射出细碎金光,将浅绿的灌木与蕨类染得透亮;溪涧从林间穿过,像条银线将绿毯裁成两半,水面漂着松针、野樱瓣,还有被溪水冲得发亮的鹅卵石。镜头拉近,百年马尾松的树皮皲裂如老茧,枝桠间垂着松萝,像老人的白须在风里轻晃;枫树的叶片正由绿转橙,叶尖挂着晨露,“啪嗒”落进溪石,溅起的水花惊醒了石缝里的螺蛳。这是天地对山林的馈赠,亦是山林对溪流的滋养——原来最好的共生,从不需要刻意维系,不过是松针落进溪涧化作鱼食,溪水漫过苔痕滋养树根,是“我活,你亦活”的朴素真理。
溪水行至此处,偏生绕了个弯。它贴着一块巨大的青石板流过,石板上刻着深浅不一的苔痕,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浅滩上支着米白色的露营帐篷,年轻人蹲在溪边洗草莓,笑声撞碎在水面上,惊得石斑鱼“嗖”地窜进石缝;阿婆蹲在溪边洗衣,棒槌敲在青石板上,“咚咚”声惊飞了停在芦苇上的白鹭。“这是蛇盘石,”她指着石面深浅不一的凹痕,“从前山洪暴发,石头被冲下来卡在这儿,藤条顺着石缝长,年头久了,倒把石头捆成了个‘绿粽子’。”她用枯枝在石上画了道弧线,“都是岁月刻的,也是溪水磨的。”我忽然懂得,所谓“历史”从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一块石头被溪水磨圆的耐心,是一根藤条缠绕百年的坚持,是我们站在当下,触摸到的过去的温度——原来“归处”的密码,就藏在这些被时光揉皱的细节里。
暮色漫上黑木崖时,溪水褪成蜜色。黑木崖是借母溪流域里最沉默的山梁,崖壁爬满深褐色的野杜鹃,石缝里钻出的几株野樱桃正红得透亮。我坐在吊脚楼的廊下,看最后一缕夕阳从林梢沉落。溪面浮着碎金,像谁把星星揉碎了撒进去;对岸的老樟树投下长影,把溪水切成明暗两半——亮的那边游着石斑鱼,暗的那边爬满青苔,石缝里钻出几株野姜花,白得像落在水面的月光。这时阿婆的声音从灶屋传来:“妹子,来搭把手!”她系着靛蓝围裙,指尖沾着灶灰,竹篓里堆着带泥的土豆、挂着露的空心菜,还有半块黑黢黢的猪后腿,最上面压着片暗红的腊肉——“今早刚从后山熏的,”她拍了拍那片腊肉,“去年冬天腌的,就等这时候用”。
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阿婆将猪后腿焯水、剁块,又从竹篓里取出腊肉,用热水泡软后切薄片。“这腊肉是用山核桃壳熏的,”她指着灶膛里跳动的火星,“柴火要选松枝,烟轻火旺,熏出来的肉才香得透。”她将腊肉片铺在砂锅底,再码上猪脚块,加山泉水、姜块、山胡椒,小火慢炖。“你闻闻,”她掀开锅盖,腊肉的焦香混着猪脚的腥鲜涌出来,“这味儿,比城里卖的腊肠实在多了。”汤面浮着透亮的油花,混着姜香、胡椒香、腊肉香,在灶屋织就一张温暖的网。另一边的石磨正“吱呀”转动,小菊推着磨盘,米浆顺着磨缝流入木盆,乳白的浆汁像溪涧里的晨雾,沾得她的小花裙都泛着湿润的白。“这是山泉水磨的米粉,”阿婆舀起一勺,“不加石膏,不掺糯米,滑嫩得能抿化在嘴里。”我伸手接住,米浆顺着指缝滴落,在阳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原来最珍贵的味道,不过是山泉水、老手艺,和一颗愿意慢下来的心。
“阿婆,今天还打糍粑不?”小菊忽然抬头问。阿婆笑着应了声,从梁上取下竹篾蒸笼,掀开盖子,热气裹着糯米香扑出来。蒸笼里的新糯米颗粒饱满,浸了一夜山泉水,蒸出来黏牙得很。“后山上的糯米,”阿婆捏起一粒,“用山泉水泡了整夜,蒸出来才黏牙。”她把糯米倒进石臼,抄起枣木槌“咚”地砸下去,糯米团在石臼里翻涌,溅起星星点点的米浆。小菊踮着脚帮忙翻糯米,木槌落下时,她赶紧用竹片翻搅,两人的笑声撞在石臼壁上,惊得梁上的燕子扑棱棱飞出去。“要这样打,”阿婆教我,“手腕要活,槌子要沉,把糯米里的空气都打出来,糍粑才软和。”在她的手心里,木槌真的听话了,一下一下,把糯米团捣得黏糊糊、亮晶晶的。我忽然想起城里的速食糍粑,包装精美却总少了股子烟火气——原来真正的“黏”,不是糖精调的甜,而是手心里的温度,是祖孙俩相视而笑的情分,是“我教你,你学我”的传承——这传承里,藏着“归处”最温暖的注脚。
暮色渐浓时,糍粑和豆腐的香气在灶屋里缠成了一团。阿婆掀开蒸笼,糍粑裹着糯米香扑出来,白得像朵云,用竹片挑起来能拉出丝。咬一口,软糯里带着清甜,倒像山涧里的风,清清爽爽的。“好吃吧?”阿婆眯眼笑,“从前知县护母那会儿,他媳妇就爱做这个,说是‘糍粑黏,人心暖’。”豆腐出锅时,豆浆表面结了层薄薄的豆腐皮,阿婆小心揭下,叠成小方块:“这是豆腐皮,泡发了炒着吃,鲜得眉毛都要掉。”我接过豆腐皮,摸起来软滑得像婴儿的皮肤,凑近闻是豆子最本真的清香——原来最动人的“鲜”,从来不需要添加剂,不过是现磨的豆浆,是守着灶火慢慢煮的耐心,是“慢工出细活”的老理儿——这些老理儿,原是刻在岁月里的“归处指南”。
夜渐深,我搬了竹椅坐在溪边。月光漫过林梢,把溪水染成银白,连溪里的石头都成了浸在牛乳里的玉,游鱼的鳞片泛着淡蓝的光。阿婆的吊脚楼亮着暖黄的灯,灯光透过竹篱笆,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像撒了把碎金。远处传来露营帐篷里的烤肠香,年轻人用树枝串着玉米,火苗舔着锅底,和柴火灶的热气不同,石头灶的火更匀,烤出的玉米带着山石的清冽。“阿姨,您家的糍粑太香了!”扎着马尾的姑娘举着保温杯跑过来,“我们刚才用溪水煮了玉米,您尝尝?”阿婆笑着接过杯子,喝了一口:“甜着嘞,和咱们后山的野玉米一个味儿。”小菊抱着粗陶碗跑过来,碗里盛着冰镇的酸梅汤:“尝尝!我阿公说,夏夜喝这个,蚊子都不敢咬。”酸梅汤甜中带酸,顺着喉咙滑进胃里,凉得人打了个激灵。我望着她眼里的星光,忽然想起城里夏夜的喧嚣——空调的嗡鸣、汽车的鸣笛、夜市的吵嚷,哪有这里的“静”来得踏实?
静,不是无声。是虫鸣织成的网,是溪水弹的曲,是松涛打的拍,是木楼里飘来的饭香,是露营帐篷里飘来的烤肠香,是石头灶上玉米的焦香,是石臼里打糍粑的闷响,是磨盘上磨豆腐的吱呀。这些声音像溪涧里的鹅卵石,被岁月磨得圆润;又像林子里的苔藓,把每一寸空隙都填得满满当当。我忽然懂了借母溪的静——这不是城市里被钢筋水泥捂住的死寂,而是山林的静,是溪水的静,是万物各安其位的静。山林用松针为溪流遮阳,溪流用清泉为山林解渴;虫儿在草叶上唱歌,鸟儿在树杈上打盹;山民在灶屋烧饭,露营者在溪边烤串;烟火气和着松脂香、腊肉香,在廊下织成一张温柔的网。所有的生命都在自己的位置上生长、呼吸、陪伴,像首没有指挥却永远和谐的乐章——原来最好的“和谐”,从不需要刻意编排,不过是“我存在,你亦存在”的自然。这自然,原是最本真的“归处”。
离别那日,阿婆塞给我一个蓝布包。“里面是昨天的猪脚粉,”她拍了拍布包,“用荷叶裹着。”我接过时,触到布料的温热,像触到了一颗滚烫的心。布包里除了粉,还躺着几块糍粑,用竹篾细心包着,还沾着点糯米香,最底下压着片薄如蝉翼的腊肉——“这是去年熏的最后一茬,”她笑着说,“你拿回去,蒸米饭时放片,香得能馋哭邻居。”车过沅水大桥时回望,借母溪已隐入苍茫翠色,唯有林梢的雾霭在阳光中浮动,像谁掀开了块绿绸子的一角。山风掀起我的衣角,我忽然想起出发前整理行李的动作——那碗猪脚粉的香气、糍粑的糯香、腊肉的焦香、豆腐的豆香早被我小心收进行囊,此刻正随着山风在车窗外飘散,混着松针的清苦、野蔷薇的甜,在记忆里酿成一坛陈酒。这坛酒,原是“归处”的滋味。
后来许多个加班到深夜的夜晚,我望着窗外闪烁的霓虹,总觉得记忆里有一缕炊烟在轻轻召唤。直到某个周末,我在厨房试着打糍粑,木槌落下时,忽然就想起借母溪的灶屋:阿婆握着我的手教我砸糯米,小菊踮着脚翻糯米团,石臼里的糯米团翻涌着,溅起星星点点的米浆;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腊肉的焦香混着猪脚的腥鲜漫出来,把整个屋子都熏得暖融融的。原来有些味道,有些温度,有些故事,从来都不是“经历过”就够了——它们会悄悄在血脉里生了根须,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提醒你:什么是真正的“家”,什么是值得用一生去守护的“暖”。这根须,原是“归处”的脉络。
当你某天路过一片山林,闻到风里飘来松脂的香气;或是深夜煮一碗热粥,看热气在玻璃上凝成水雾;又或是在露营帐篷里,听着溪水声啃着烤肠——你就会忽然明白:借母溪从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它是天地间的一片净土,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片归处。它教会我们:最好的生活,不在远方的喧嚣里,而在眼前的烟火里;最珍贵的永恒,不在时间的长度里,而在情感的深度里;最动人的乡愁,不在记忆的模糊里,而在每一次想起时,心底泛起的那阵温暖。这温暖,原是“归处”的心跳——是阿婆灶屋里的腊肉香,是石臼里的糍粑响,是溪水边的烤肠摊,是所有被记住的、细碎的、鲜活的,关于“活着”的模样。
这,或许就是借母溪给我的,最深刻的感悟——原来我们穷尽一生寻找的“归处”,从来不在远方,而在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最本真的活法里:是松针与溪石的默契,是阿婆与小菊的传承,是烟火与自然的共生,是每一片腊肉里藏着的、被时间吻过的,关于“家”的答案。它一直在那里,等我们放下匆忙,弯下腰,轻轻拾起。


李骥,汉族,湖南省耒阳市人,现居长沙市,供职省直某单位。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省湘水余波诗社、鹿歧诗社成员,诗词、散文、随笔作品散见各报刊网。
来源:红网
作者:李骥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化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