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向内心深处那片永不枯竭的蓝海
——李立组诗《皇后镇的风儿有点甜》读后感
文/龙晓初
当大地成为文本,诗人即为读者
“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此语出自清代文人张潮《幽梦影》,寥寥数字,却道尽了中国古典文学与自然之间那层深邃而温润的精神联系。然而,在今日这个被算法切割、被流量裹挟的时代,我们是否还能听见山河低语?是否还愿以脚步丈量大地?是否仍相信一首诗可以唤醒沉睡的星空?
值得庆幸的是,诗人李立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确凿的答案。
我初识李立,并非因其声名显赫,亦非因某次文学盛典上的惊鸿一瞥,而是通过他近年来持续不断、近乎执拗地游历世界所留下的诗篇。这些作品如星子散落于南半球的海岸线、北境雪原的冰川之上、太平洋岛屿的密林深处,以及人类文明边缘地带那些尚未被过度阐释的风景之中。它们不是旅游手册式的轻描淡写,也不是地理志中的冷峻记录,而是一种深刻的“地理诗学”实践——一种将身体经验转化为精神图景、将空间位移升华为心灵迁徙的语言仪式。
因此,当我读完他的组诗《皇后镇的风儿有点甜》(共11首)后,心中涌起的第一个判断便是:李立是中国当代真正意义上的“行吟诗人”。
但这里的“行吟”,绝非对唐代孟浩然“骑驴觅句”式浪漫主义姿态的简单复刻,也不是贾岛般苦吟推敲的孤高清冷;它更接近一种现代性的存在方式——一个自觉选择“在路上”的生命个体,用行走对抗虚无,以抒情回应荒诞,在广袤天地间寻找自我归宿的同时,也重新定义了诗歌的功能与使命。
下面拟从四个维度展开评述:其一是李立作为“行吟诗人”的精神谱系建构;其二是其“地理诗学”的审美特征与哲学根基;其三是他对信仰、生死、人性等终极命题的诗意追问;其四是其语言风格中所蕴含的智性光辉与情感温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在一个日益技术化、虚拟化的时代,为什么我们需要像李立这样的诗人?
“行吟”的当代转型:从古典意象到生存实践
在中国传统诗学中,“行吟”从来不只是动作本身,而是一种高度象征化的精神姿态。屈原“行吟泽畔,颜色憔悴”,杜甫“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苏轼“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些诗句背后,皆隐含着士人阶层在政治失意或人生困顿时,借山水寄情、托天地自遣的文化心理机制。
换言之,古代“行吟”本质上是一种退守策略——当无法改变现实时,便转向内心世界寻求慰藉。它带有浓厚的避世色彩和道德洁癖。
而李立的“行吟”,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他的行走不是逃避,而是主动出击;不是消极放逐,而是积极介入。他不回避世界的复杂性,反而迎难而上,深入异域文化腹地,直面生态危机、战争创伤、身份认同等现代性命题。他的诗中没有故作高深的玄思,也没有无病呻吟的哀叹,有的只是真实的身体感知、敏锐的情绪反应和朴素的价值立场。
没有阳光攻不破的冰雪与谎言
没有正义战不胜的阴谋和邪恶
这种典型的“及物抒情”——情感不悬浮于空中楼阁,而是牢牢扎根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正如他在《狩猎》一诗中写道:“我听见一种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急促,像是大海的心跳/又像是发自鹿,或者是我自己的内心。”此处的“心跳”既是生理体验,也是良知震颤,更是诗人与万物共鸣的生命律动。
由此可见,李立的“行吟”已超越了个人情绪宣泄的层面,上升为一种具有伦理指向的审美行为。他不再仅仅是个体情感的代言人,更是全球视野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见证者与传达者。
“地理诗学”的建构:空间如何塑造语言
如果说传统诗歌强调“情景交融”,那么李立的创作则进一步发展为“地情互渗”——即地理环境不仅影响诗人的情感表达,甚至直接参与诗歌意义的生成过程。
这种写作范式,我称之为“地理诗学”。
所谓“地理诗学”,并非指单纯描写山川地貌的“风景诗”,而是指诗人通过对特定地域的空间感知、文化理解与历史记忆的整合,构建出一套独特的认知框架与话语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河流、每一片草原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承载着多重象征意义的“文本”。
李立的诗正是如此。他笔下的“米尔福徳峡湾”“伊甸山”“瓦纳卡湖”等地点,早已不再是地图上的坐标点,而是被赋予了精神重量的文化地标。
以《去米尔福德峡湾的路上》为例:
镜湖不大,却可以装下整个南阿尔卑斯山
包括岩石、树木、啄羊鹦鹉、喜玛拉雅山羊
还有蓝天,需要修炼多久才拥有如此强大的雅量
这里,“镜湖”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湖泊,更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容器”——它象征着心灵的包容力与精神的澄明境界。诗人借此提出一个深刻问题:一个人要经历多少沉淀,才能像湖水一样平静地映照万象?
再看《伊甸山》:
把一个个高高隆起的错误,悉心改造
时间,是治愈一切伤口的灵丹妙药
在大自然自赎的神来之笔中,我们是唯一的败笔
这首诗将火山地貌与人类历史并置,揭示出自然具有强大的修复能力,而人类却常常在重复错误。所谓“高高隆起的错误”,既可指地质活动形成的火山锥,也可暗喻战争、殖民、生态破坏等人祸所留下的创伤。结尾一句“我们是唯一的败笔”,堪称惊心动魄——它不是悲观主义的哀鸣,而是清醒者的自我批判。
这种将地理现象转化为哲学隐喻的能力,正是李立“地理诗学”的核心所在。他并不满足于“看山是山”,而是追求“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三重境界。他让我们意识到:当我们凝视自然时,自然也在凝视我们;当我们书写大地时,大地也在书写我们。
这一点,恰与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观点不谋而合。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指出:“自然之道就是十字架之道。”他认为,荒野不仅是生物栖息地,更是精神成长的场域。人在面对原始自然时,会重新思考自身的位置与价值。
李立正是这样一位“走向荒野”的诗人。他放下身段,放弃以人为中心的傲慢视角,转而倾听蚂蚁的低语、敬畏胡杨的坚韧、欣赏雪豹的自由。在他的诗中,动物不再是被动的观赏对象,而是拥有尊严的生命主体。如《写给一只在米尔福德峡湾戏水的海豹》中写道:
相信风中无法生成伤害,所有的眼眶里满溢着怜悯与善良
世界深浅难测 ,我的热爱始终未变
这是何等纯净的目光!诗人不再居高临下地“描写”海豹,而是以平等的姿态与其对话,甚至试图进入它的感知世界。这种“通灵式”的书写,使诗歌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展现出一种泛灵论般的宇宙情怀。
信仰的锄头:在漂泊中重建精神家园
如果说“行走”构成了李立诗歌的形式骨架,那么“信仰”则是其精神脊梁。
在他看来,真正的旅行,从来不是身体的位移,而是灵魂的朝圣。正如他在《地窝子》中所赞美的那样:“相信盐碱地,硬不过信仰的锄头。”这一比喻极具震撼力——“信仰”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成了劳动者手中实实在在的工具,既能开垦荒漠,也能挖掘希望。
这让我想起木心在《同情中断录》中的题辞:“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这句话充满悲情,但也道出了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存在性空虚”——许多人终其一生奔波劳碌,却从未真正活过。
而李立的诗歌,则提供了一种对抗这种虚无的方式:通过信仰的确立,赋予生命以方向与重量。
他的信仰并非某种具体的宗教教义,而是一种关于生命尊严、人性光辉与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这种信仰体现在他对平凡生活的深情礼赞中,如《皇后镇的风儿有点甜》:
晚霞下湖畔灿烂绽放的婚纱、笑靥和春光
酿造着人间的浓情蜜意,皇后镇的风儿有点甜
沙滩上的默默依偎,人潮中的十指紧扣
搀扶前行的童颜鹤发,无不都散发出幸福的味儿
这里的“甜”,不只是感官体验,更是一种心灵感受。诗人捕捉到的是日常生活中最朴素却最珍贵的情感瞬间——爱情、陪伴、相守。他告诉我们:即使身处异国他乡,最美的风景依然是“烟火人间”。
与此同时,他也敢于直面死亡与牺牲的主题。在《激流岛顾城故居》中,他写道:
一个中国诗人的一双黑眼睛,没有发现光明
世人只看到了,激流岛最黑暗的那一页
这首诗是对顾城悲剧结局的沉痛反思。李立没有美化暴力,也没有回避责任,而是以冷静笔触揭示天才陨落背后的深层原因:当理想主义走向极端,便会变成毁灭性的疯狂。但他并未因此否定诗歌本身的价值,相反,他更加坚信:唯有健康的信仰,才能避免艺术沦为暴政的帮凶。
由此观之,李立的信仰观兼具理性与温情。他既反对盲目的狂热,也拒绝冷漠的犬儒。他倡导的是一种“雅正的信仰”——不高蹈也不媚俗,不偏激也不麻木,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这也呼应了海子那句著名的话:“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李立的诗虽无燎原之势,却有一种“月白风清”的高旷情怀。他不煽情,不炫技,只是静静地观察、真诚地表达。正因如此,他的文字才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
语言的艺术:清兴与清狂之间的平衡
评论一位诗人,最终还是要回到语言本身。
李立的诗语风格可用两个关键词概括:清兴与清狂。
“清兴”源自古人对高洁情趣的追求,如“睹标志,发怨俗之兴,见精洁,动出尘之想”。李立诗中常见此类意境:雪山、湖泊、飞鸟、晨曦……这些意象构成一幅幅空灵澄澈的画面,令人“如临秋水,如坐春风”。
但若仅止于此,则易流于唯美主义的肤浅。可贵的是,李立并未沉溺于形式之美,而是在“清兴”之外,另辟“清狂”一路。
所谓“清狂”,是指一种不受拘束、率性而为的精神气质。他在《皇后镇的风儿有点甜》中写道:“喷射船、激流泛舟和跳伞,甚至发明蹦极/试着挑战爱情的极限,贪图刺激/信任难免受伤。”这哪里是温婉的吟唱?分明是带着冒险精神的生命呐喊!
又如《桅杆写给帆的情书》中那一连串排比句:“你有多婀娜我就有多魁梧,你有多俏丽我就有多挺拔”,情感炽烈,气势磅礴,颇有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迈气概。
正是在这种“清兴”与“清狂”的张力之间,李立的语言获得了独特的节奏感与表现力。他既能写出“镜湖不大,却可以装下整个南阿尔卑斯山”这样静谧深远的句子,也能挥洒出“风只为张开的翅膀壮行”这般激昂奋进的宣言。
此外,他还善于运用跨文化意象进行对话。如《玛塔玛塔随感》中提到《指环王》拍摄地,巧妙融合童话叙事与现实批判:
山脚那些迷你房舍,其实就是一个个伪装的谎言
门一概虚掩,入戏的人们都不愿推开真相
这是对旅游消费主义的深刻讽刺,也是对现代人沉迷幻象的心理剖析。诗人借用电影布景的“虚构性”,反衬出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真相的集体回避。
全诗结尾处:“善恶自然泾渭分明/阳光奋力拨开云雾,天际的底色始终如一地蔚蓝”,看似乐观,实则蕴含警醒——唯有坚持正义与真诚,才能穿透表象,抵达本质。
诗歌是一次永不抵达的归来
最后,我想引用印第安人的谚语作结:“放慢你的脚步,好让灵魂跟上你的步伐。”
这句话,或许正是李立诗歌的最佳注脚。
他的每一次出发,都不是为了逃离,而是为了更好地归来;他的每一首诗,都不是终点,而是一次新的启程。他像徐志摩那样“轻轻地来,轻轻地走”,不留痕迹,却满载心灵的收获。
他走过万水千山,归来满脸沧桑,行囊空空,但内心欢悦明净。这不是齐奥朗式的虚无主义,也不是尼采式的超人哲学,而是一种东方智慧中的“知足常乐”与“返璞归真”。
在这个人人急于发声、争相打卡的时代,李立提醒我们:真正的诗意,不在热搜榜上,而在你放缓脚步时听见的风声里。
他的诗,是一座桥梁,连接着自然与人文、个体与世界、当下与永恒。他让我们明白:行走的意义,不在于征服多少土地,而在于让土地改变我们。
所以,请允许我再次强调:
李立,是这个时代最值得尊敬的行吟诗人之一。
他的诗,不是修辞的装饰,而是生命的证词;
他的路,不止通往远方,更通向内心深处那片永不枯竭的蓝海。

龙晓初,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汕尾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潮》《延河》《诗林》《中华文学》《阳光》《中国民族报》《中国建材报》《北京日报》《南方日报》等报刊杂志。


李立,著名环球旅行家,环中国大陆边境线自驾行吟第一人,足迹遍及7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文学批评家喻为“中国当代最经典的行吟诗人”“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第一行吟诗人”。作品见于《诗刊》《人民文学》《花城》《创世纪》等100多种主流报刊,获博鳌国际诗歌奖、杨万里诗歌奖和悉尼国际诗歌奖等十数次。《中国行吟诗歌精选》年度选本和《中国行吟诗人文库》诗丛主编。出版诗集、散文随笔集和报告文学集共7部和英文诗集1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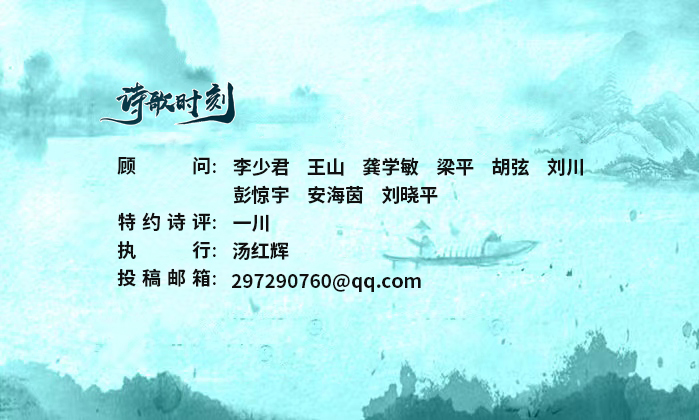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龙晓初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化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