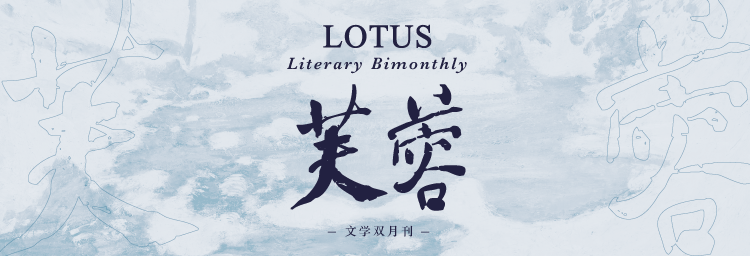

你们的名字
文/舒飞廉
深秋时节,晴天的话,五点半就可以出门散步,这时候夕阳快落到澴河堤上,晚霞璀璨,明亮的光辉里,已经含有一股凉意。向西走,经过保明、保刚家的门口。我家门前的竹子蔓生有一百多竿,八月父亲由南宁我弟弟家回返,为塆北头他姨母奔丧,顺便用我的电锯,将竹子伐掉了一大半,晚上我在床上听风吹竹林的淅沥潇飒,声势也少了一半。保明家的桃树春天开花,夏天结果,红桃子啪啪掉到地面,有一根桃枝伸臂到路上,我忙活一早晨,用柴刀砍断了,他家还有一棵栀子,跟桃树一样,有好几个树瘤,二三十年树龄总有吧,夏天也能开几百朵花,村里十来个大嫂与老太太,天天来摘,也摘不完,何况她们自己家门口又不是冇得。
保华家廊前的两棵枣树也是,初秋时结出枣实,像挂毯似的罩满树身,保华妈云英婶一见我,就指着请客,让我摘枣子吃,我摘一把,她在树下的机井边压机械臂打水,我满捧着枣子,流水洗洗就可以吃,味道不错的。我们两个,哪里吃得完呢,大风吹枣子落,微风吹枣子落,无风枣子也落,一堆标点符号,织地毯似的围在水井边,还要劳烦云英婶扫,一天一撮箕。竹子、桃子、栀子花、枣子还在繁荣上进,奈何村里常住人口日渐变少,你们要是能改性成春节里开花结果,可能会稍好一些,小孩子如正在驯化中的猴儿归山,青壮年回来打尖,随手掐花摘果,就不会这样白白浪费你们的盛意。
沿我们村祠堂东墙下的水泥路往北走二三十米,再向西拐,就是往两公里外澴河去的马路。祠堂北墙下栽的是桂花与紫薇,大路与北墙之间,是一片水泥空地,村里老人去世,这里是追悼与吃席的道场。拐弯的地方,路北是牛背形的绿色铸铁垃圾箱,印有“肖港镇环卫”的字样,人家有编制,吃商品粮,早晚会有穿黄马甲的师傅戴手套来收拾打理。路南立起来一块石碑,碑上刻着二十多年前,捐修祠堂与村中道路的村人的名字,石碑后面,是十来株枫杨、水杉、毛白杨,高大挺拔,树下是接骨草、商陆、艾蒿、狗尾草、苍耳等蒿菜野草,余晖返景,一片秋色。碑上密密麻麻的字迹,也被带着红晕的光线映照得清清楚楚,蚊子脚、蜻蜓翅、蜘蛛网一般,纤毫毕现。夏天的傍晚我路过这里,树林里蝉声如雨,晚一点的话,草丛深处还会有秧鸡鬼魅的吟哦。
我也会在石碑前站站,读一读上面的名字,唉,我估计,在它并不算太多的读者里,我就是那位“理想读者”。这些名字是我们村男人们的“大号”,按字派配置出来的,我们都姓郑,此番正在使用的字派是“礼法文章,永保家邦,怀仁守义”十二个字,一个字管一世,一世三十年,够用三百六十年的。我轮到的是一个“保”字,父亲“永”,祖父“章”,我儿子按理是“家”,孙子是“邦”。所以石碑上的名字,郑永某、郑保某、郑邦某最常见,“章”字刻在更远处我们祖坟地的墓碑上,郑怀某、郑仁某们还在前来投胎的路上,但我估计,我们这个村塆也不太可能成为他们的投胎目的地了,他们在外面的城镇啼世,也会从这些字派的血脉铰链里逃逸,去注册“梓豪”“浩轩”“宇航”之类的鼎鼎大名。就是石碑上努力刻的一百多个名字,它们所指的主人,有一半已经死了,经过旁边道场上道士们主持的悼亡,去往黄泉暂住,如保明。另外一半,或肖港镇,或孝感市,或武汉市,士农工商,绝大多数,或工或商,散落各地常住,如保刚,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这一辈,按姓氏字辈加上第三个字的发挥,取好名字,这个名字大概就会随我们进学校,填户口本,办身份证,刚开始写在作业本、试卷上,觉得怪怪的,小学老师用蹩脚的普通话喊出来,也是蛤蟆惊出一身油,到后来,也安之若素,想必最后送往医院救护时,会达到人名合一的境界。我父亲他们一辈,再往上,则有不同,他们大号是大号,用于族谱与碑铭,他们另外还各有小号与绰号,绰号是由他们在伙伴中间的劳作或游戏活动里得来的,小号则用在日常生活中,说起来,有一点像从前文人们的“表字”与“号”,被长辈和同辈呼喊,晚辈则加上“爹”“伯”“叔”等,或者后来办身份证,填写各处的表格,其实是用“表字”作为名字。
这些名字作为能指,与他们的音容笑貌合在一起,可能比“大号”更有效,可惜在石碑上读不到:这是只在他们此生、此地陪伴他们的名字。国平、国安、国庆、国华、国成、富平、平均,一看就是一批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哇哇落草在共和国的朝晖里,建桥、建林、建华、建初,可能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这些名字里,可以听到当年修水利的口号,公社有线喇叭里的嘈杂。这是一些跟上“形势”的名字,还有几个系列,小时候我觉得古里古怪,现在想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
(节选自2025年第3期《芙蓉》舒飞廉的散文《你们的名字》)

舒飞廉,原名郑保纯,湖北孝感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现居武汉。出版有《飞廉的村庄》《绿林记》《射雕的秘密》《云梦出草记》《万花六记》《云梦泽唉》等作品。
来源:《芙蓉》
作者:舒飞廉
编辑:刘铮
本文为文化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