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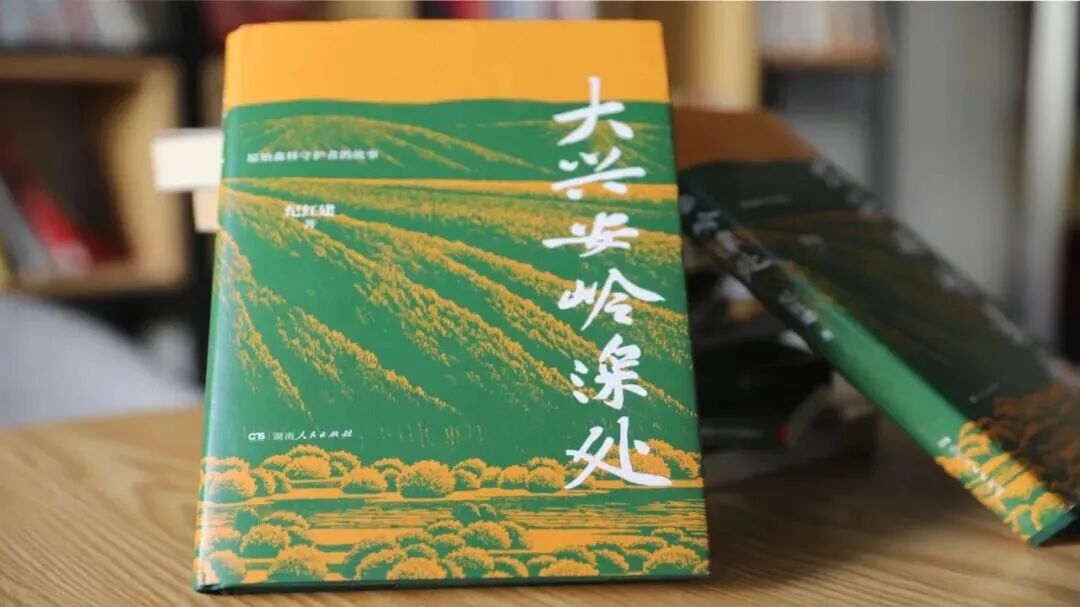
2024年度生态文学推荐书目
纪红建长篇报告文学《大兴安岭深处》
阿巴河畔不眠的倾听
文/纪红建
大兴安岭的夜,宁静纯美。
看不到任何人为的光线。
风吹林海的阵阵“涛声”,阿巴河潺潺远去的流水声,偶尔树枝“咔嚓”的折断声,还有细微的虫鸣声……
这种宁静,这种纯美,令初次踏入这片土地的我沉醉不已。
“汪汪!”
“汪汪!”
……
深夜十一点多,营区前突然传来一阵狗叫声,荡漾在茫茫夜色中。
最开始只有一条,后来又有其他同伴加入。两条,三条,四条,或者五条。它们边叫边跑,边跑边叫,越叫越勇,越叫越凶……
在奇乾中队的第一个夜晚注定无眠。
这是2021年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是头一天从长沙乘飞机到达海拉尔的。第二天一大早,在内蒙古自治区森林消防总队大兴安岭支队宣传科相关负责同志的带领下,我爬上越野车,赶往奇乾。近10个小时的行驶中,我们一直穿行在茫茫的绿色海洋。一路上,我感受到大兴安岭的多彩绚丽、浩瀚广阔,也感受到这里忽晴忽雨的独特的小气候。奇乾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下辖乡,地处额尔古纳河畔,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森林腹地;而隶属于大兴安岭支队莫尔道嘎大队的奇乾中队,不仅身处祖国北部边疆最前沿,还守护着我国95万公顷唯一集中连片的未开发原始林区。
当我们穿过茫茫密林到达中队时,已是傍晚。苍茫的暮色,渐渐隐没了远处的山峦。红色屋顶、白色墙面的营房呈凹字形嵌在森林深处,食堂的烟囱冒着炊烟,眼前的一切是那么整齐、干净,让人顿生好感。几条黄的、黑的大大小小的狗,飞快地跑了过来,热情地摇着尾巴。
晚饭后,中队指导员王德朋带我参观中队荣誉室。王德朋是个“90后”,戴着眼镜,帅气而又斯文。来自呼伦贝尔扎兰屯市的他2008年考上北京林业大学的国防生,毕业后他选择了大兴安岭,在库都尔大队待了四五年后,他回到北京林业大学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他又毫不犹豫地投入大兴安岭的怀抱,并义无反顾地来到奇乾中队。不少同学和朋友说他傻,读完研究生明明有机会走出大山,他却在大兴安岭越走越远、越走越深。
荣誉室不大,但我却感受到它的厚重与分量。王指导员说,每年新队员下队,中队都要利用参观荣誉室的时机开展队史教育,用创业的艰辛历程、用一块块沉甸甸的奖牌激励他们扎根林海腹地,用一茬茬奇乾人几十年来积淀形成的奇乾精神感召他们、熏陶他们。中队不仅责任和使命重大,而且历史悠久。大兴安岭是祖国北疆的“绿色长城”,不仅抵御着西伯利亚寒流和蒙古高原的寒风,还是巩固东北平原的天然屏障,守护着“中国大粮仓”松嫩平原的粮食生产安全,生态价值特殊而重要。奇乾中队守护的这95万公顷原始林区,地处大兴安岭的北部,是欧亚泰加林带东西伯利亚泰加林在我国境内唯一延伸部分。如果按中队人数平均算下来,每个人的防火区有两万多个足球场那么大。概括起来说,奇乾中队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地处边境线旁。中队驻地离中俄边境只有2.5公里,这对广大指战员忠诚度的考验直接而严峻;其二,地处冷极线上。中队驻地位于祖国版图鸡冠处,年平均气温零下3摄氏度,最低气温历史记录达零下53摄氏度,全年无霜期平均只有82天,冬季长达9个月;其三,地处林海腹地。在整个大兴安岭消防支队,奇乾中队防区最大、任务最重、年平均参加打火次数最多。中队于1963年4月成立,从成立之日到今天,在大兴安岭守护了大约二万二千个日夜。可以说,在这里,队员常年与大山为伍、与密林为伴、与寂寞抗争。离这里最近的乡镇是莫尔道嘎镇,距离中队驻地有150多公里;这里一年有6个月大雪封山,白雪皑皑;中队驻地人迹罕至,不通常电,不通邮政。
冬天挑战的是生存极限,夏天则考验着打火水平。什么是打火?其实就是灭火、扑火,但队员们都习惯叫打火,叫起来更加亲切,更加带劲。大兴安岭的夏天虽然很短,却是火灾的高发期。主要是雷击火,人为火极少。特别是6月到8月,是干雷暴高发期。北部林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地质构造和气候环境,极易引发干雷暴。加上这里到处是油脂含量高的松树,一旦发生干雷暴,就有可能引发森林火灾,且易燃难扑。有一天,北部林区打雷多达一千多次,可能是有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天。前几天,驻地打雷了,一个小时里扎扎实实打了 40 分钟的雷,是雷暴,电闪雷鸣的。只要听到雷声,队员们心里就会担忧,就会警惕起来,做好打火的一切准备。打雷下雨还算好,电闪雷鸣伴随着降雨,且降雨量达到一定强度后,打雷引发的火灾可能就会自动熄灭。怕就怕干雷暴。要是干雷暴,或者雨量太小不能熄灭火源,火源就会蔓延成灾。这里山高林密、灌木丛生,在外人看来是那么神秘与奇妙,但却是打火难度极大的地区。
“打火一定很危险吧?!”我说。
王指导员平静地说,和平年代,打火就是“战争”。“我们手里虽然不拿枪,但是拿着打火用的风机。风机上的风筒就是我们的枪。拿着它上火场,感觉就像上战场打仗。打火是森林消防队伍存在的意义,虽然我们是那么渴望没有火灾。”
林火分为树冠火、地表火和地下火。其中以树冠火的扩散最为迅猛。火在树冠上燃烧,火头往往有十几米高,借着风势,从一棵树烧到另一棵树,在林子里肆无忌惮地游荡。队员们抵达火场后就立即开始打火吗?不是的。风大、温度高的时候,火势最猛,这时候一般不直接打火,因为火势难控制,危险性很大。怎么办?指挥员马上勘察地形和天气,预测过火面积,确定隔离带的建立位置。队员们则根据指令,砍倒林木,挖沟,打出隔离带,把大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啥时候向“火魔”进攻呢?往往在风力变小、气温下降时开始。老队员组成尖刀班,冲在前面,背着风力灭火机打火头,年轻队员则跟在后面清理余火。打火时最痛苦的是缺水。长时间靠近烈火,会造成人体水分加快流失。有经验的老队员格外珍惜带的水,无论多渴,每次都只抿一小口。一些年轻队员没经验,还在前往火场的路上,就喝完了自带的水。有经验的班长会给年轻队员支招:用刀划开桦树皮,插入一根木棍,引出水分,用瓶子接住。个把小时后,就能接三四厘米深的桦树汁。大家分了,每人抿一口。但只是杯水车薪,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派队员寻找水源。在火场,“扣头”是最动听的一个词。“扣头”的意思是分布在不同火线的队伍实现碰面,这意味着队伍完成了对火线的合围,火势得到了控制。火场上能见度不高,打火的队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扣头”。只有观察整体火情之后方能察明一切。他们会通过对讲机告诉火线上的指挥员:某某中队注意,前方多少米是某某中队,马上实现“扣头”!这声音传来时,大家就知道,终于能从火的地狱回到温暖的人间了。
夏天不仅干雷暴频发,还蚊虫肆虐。最常见,也最可恶的是草爬子。这家伙个头只有芝麻那么大,呈椭圆形,没吸血时腹背扁平,背面稍隆起。你别看它小样儿不咋地,名字却有好几个,学名叫硬蜱,别名叫扁虱、壁虱,俗称草爬子,是寄螨目、蜱总科。这小家伙不仅名字多,能量更是大得很。它是嗜血的寄生虫,专叮比它大得多的“庞然大物”。吸血前,它比蚊子还小,吸血后能变成赤豆一般大。要是被它叮咬,它会将头钻到皮肤里,不断地吸血。如果发现及时,还能够将头一起拔出;待它变得赤豆那么大了,就不好拔了,很有可能头会留在体内。其实被吸点血不算什么,可怕的是这可恶的家伙在吸血的同时会分泌毒素,有可能导致被叮咬的人出现高热、呕吐、昏迷、关节疼痛等现象,严重时甚至威胁生命。要是这家伙的头留在了体内怎么办?得赶紧把它弄出来,不能让毒素留在体内,更不能让其扩散。奇乾中队的队员们几乎都有被草爬子咬过的经历,但他们不怕。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到大兴安岭,就会打森林脑炎疫苗。再说每当7月底8月初时,草爬子就会长上翅膀飞走,不再咬人。森林里还有蚊子、小咬和瞎蠓,虽然它们不像草爬子那样有毒,但更令人讨厌、烦躁。早晚蚊子和小咬跟着叮,中午瞎蠓跟着叮。瞎蠓飞得快,就连训练跑步,它都能紧追不舍。蚊子咬了鼓个包,几个小时就消掉了;小咬咬了鼓个包,要三四天才能消掉;瞎蠓咬了会肿得像拳头一样大,要一个星期左右才能消掉。外出打火时,队员们都是全副武装,使它们没有可乘之机。外出干活时,队员们都会想办法把头和面部罩住。但站岗和晚点名时,还真是不可避免被咬,只能靠自己的意志力扛下来。一班岗下来,能拍死上百只瞎蠓。晚点名时,队员们站着标准的军姿一动不动。这时,能听到蚊子“嗡嗡”飞来的声音,然后落在他们脸上,清晰地感觉到被吸血的过程。
……
(节选自纪红建长篇报告文学《大兴安岭深处》)

纪红建,湖南望城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联主席团委员。著有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哑巴红军》《彩瓷帆影》《大国制造》《游学·1917》等二十余部,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宣部第十五届“五个一工程”特别奖、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等。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来源:红网
作者:纪红建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化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