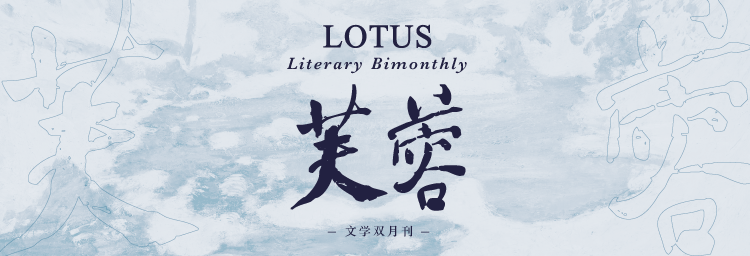

鹧鸪飞
文/傅菲
白花缀在枝丫间,流风回雪。木荷高大,冠盖如蓬,在山冈布起条状林带,包围了方家村。罗昌河穿过丘陵地带,在田野回旋、浪荡,平平仄仄,弯过方家村狭长的山前,一路向南曲流,注入白荡湖。河四季长流,野性、奔放,大音希声。绵雨之季,雨水浇在河面,嗒嗒咚咚。村人沿河挖塘,种藕养鱼。方国胜等雨歇,雨却一直下着,苦熬了两天,骑着摩托车来找我。他冒冒失失地脱下雨衣,挂在我门架上,说:“傅哥,铜陵市人民医院有熟人吗?”他的语音颤颤巍巍,半低着头,轻轻地跺脚,抖落鞋面上的水珠。裤脚湿淋淋,裹在下半截小腿上。
我泡了一杯茶递给方国胜,问:“有什么事呢?”
“我要做个手术。越早做越好。”
“做什么手术?”
方国胜抱着自己的脸,低下了头,双肩抖动了起来。他的头发不停地往下滴水。我给他毛巾擦头发,说:“缓缓气,慢慢说。”他的喉结在蠕动,费劲地上下抽拉。他说:“以后我说不了话了,说不了话了,说不了话就不是个人了。”
“好好的人,怎么会说不了话呢?别惊吓自己。”我说。
“我喉咙难受,吃饭难受,吞水难受,说话难受。我以为食道发炎了,吃了阿莫西林,吃了金嗓子喉宝,吃了一个多月,止不了喉咙难受。上个星期四,我去枞阳县人民医院检查,医生说我声带长了瘤。瘤一定要割,瘤再大一些,就压迫气管了。瘤不割就会憋死自己。”方国胜说。
“割了,就没办法说话了。”我惋惜地说。我又安慰他:“不过,不影响你体质,还可以好好生活。”
“一个人不能说话了,就会被人取笑,失去很多尊严。”方国胜说。
我逗趣他,说:“在手术之前,你把要说的话全部说完,说个三天四夜,跟认识的人打一遍电话,想骂就骂,想哭就哭。对你的妻子孩子,一遍一遍地说爱他们。与你有隔阂的人,你主动去化解误会。这样,你以后就少了很多难受。”
“一辈子的话,要用一辈子去说的。哪有集中几天时间说完一辈子的话呢?傅哥,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说话是一个连续不断发生的过程。呼吸停止了,人才不用说话了。说话和吃饭一样,伴随一生。说话和用手做事一样重要。”
“傅哥,你还是没有完全明白。”
方国胜有些委屈,不接我的话了,问:“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个好医生吧,我尽快去手术。手术不能拖下去了,我喉咙天天难受。”
我说,“我明天给你回话吧。”
声带结瘤,可真不多见。方国胜是个话痨,见了狗也可以说半天话。村里没有他不知道的事,也没有他不敢说的话。他的嘴巴张得很开,上下唇厚,说话语速又快。村人不叫他国胜,叫他炮嘴。
出了我家院子,他又问我:“你知道哪里有笛子买吗?”
“你买笛子干啥?”
“笛子当然是用来吹啊。以后,我说不了话了,我就吹笛。”
“你会吹笛?看不出来呢。”
“我十来岁的时候,我妈想我做个笛师,领着我拜了村里笛师做师父。我吃不了那个苦。”
去了东湖路和韵乐器店,方国胜看着琳琅满目的乐器,有些失落,说:“傅哥,我们还是回去吧。我不买了。”他捏着口袋,眼睛盯着置物架上的笛子。笛子有十几个品类,长短粗细不一,材料也不一样。我取了一支灵声牌董雪华8883精品苦竹笛子,在手上把玩了起来。笛管由老苦竹制成,笛头笛尾由牛角包箍,铜合金包双插接口,内壁灌红漆,外色深棕,白色扎线,长约六十二厘米。竹笛掂在手上,沉沉的。我递给方国胜,说:“你看看这个笛子怎么样?”
“这么贵的笛子,当然是好笛子了。不用试就知道。”方国胜说。
店主挨在我们身边,说:“你想买的话,我打个折。”
方国胜说:“我还是回去自己做一根笛子吧。”
跟店主讲了价钱,打了七折,还得五百三十六块钱。我用红绸布包了笛子,送给方国胜。他怎么也不肯收。我说:“我在你家喝了十多次茶,你也没收过我钱,算是我留给你做纪念吧。”方国胜要了笛膜,粘在笛膜孔上,舔了舔舌尖,吹了起来。前奏旋律线条简洁流畅,低缓婉转。吹了半分钟,方国胜就放下了笛子,说:“我从没吹过这么好的笛子。”
“你怎么不接着吹下去呢?”我说。
“曲有些长。”方国胜说。
“我听出了,这是名曲《鹧鸪飞》。”我说。
方国胜拉开衣服,将笛子插进衣内,拉上拉链,骑上摩托车往东而去。天灰蒙蒙,雨丝似有似无。莲荷在湖里吐出幼叶,青青绿绿。街道飘着零零散散的雨伞,浮萍似的。我有些难过。
方国胜幼年丧父,一家生活难以为继。他十一岁时,和八岁的弟弟国安离开了枞阳县方家村,随他妈去了浙江开化县古田村继父家生活。古田村处于古田山腹地,与江西婺源、德兴及安徽休宁交界,被崇山包围,出产木头、木炭和香菇、茶叶。年年腊月初,他妈带着国胜、国安回方家村,来各家走走、坐坐。他妈对孩子说:“方家村出的苗就要长在方家村的地上,你们长大了就回自己的方家村。不要忘了邻里,也不要被邻里忘了。”他妈脸大,声音洪亮,笑起来很畅快,鸡都会被吓跑。
古田距方家村有三百多里路,翻山到婺源江湾镇,等班车去屯溪,在屯溪住一夜,再坐车去铜陵市,坐渡船过长江去枞阳县。方国胜多次和我谈起坐渡船。严冬,江风凛冽,刀片一样刮脸。渡船上,一半堆货,一半载客。他妈左手拉他,右手拉国安。国安看到抛起的浪头,就惧怕得大哭。他背一大包柿饼,看着浪涛滚滚的大江,心一阵阵抽紧。柿饼是他妈给邻居的伴手礼。他十五岁那年冬,他家三人回方家村,在铜陵老渡口,天下起了鹅毛大雪。雪密集,大地白茫茫,江面白茫茫。渡船装货太多,延时了。过了长江已是华灯初上了。班车停了,他妈带着他和弟弟,从横埠沿着长江圩堤走,走了十多公里,才到了方家村。国安饿着了,走不动,方国胜便背弟弟。走着走着,他妈低泣了起来。
(节选自2025年第3期《芙蓉》傅菲的散文《鹧鸪飞》)

傅菲,资深田野调查者,专注于乡村和自然领域的散文写作,出版散文集《元灯长歌》《客居深山》等30 余部。曾获三毛散文奖、百花文学奖、芙蓉文学双年榜(奖)、储吉旺文学奖、方志敏文学奖、江西省文学艺术奖,以及《北京文学》《长江文艺》《山西文学》等多家刊物年度奖。
来源:《芙蓉》
作者:傅菲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