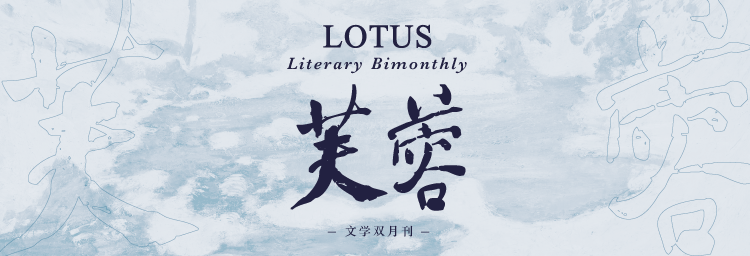

牵一匹马或一朵云(中篇小说)
文/余一鸣
付文化给我打电话,用的是一个陌生号码,一般来说,不是我通信录名单上的来电,我都不接,包括座机来电。可是,那个号码后面的人很执着,打个不停,我掐一遍他再打一遍,我只得接了。我正要骂人,电话里的人抢先说话了,说:“豁牙,我是文化。”“豁牙”是我小时候的绰号,我爷爷是大队支书,我是村上代销店的主顾,我爷爷闲着的时候,就驮着我上代销店消费。一个破小店能有什么好吃的呢?冰糖、水果糖、砂糖饼之类,我的牙齿顺理成章地变成了蛀牙,前赴后继地牺牲了,好在那时我小,还有一次换牙的机会,等到我新牙补缺,我也门面一新的时候,我的绰号却已经挥之不去,它永远活在村人们的心里,永远活在付文化的嘴上。付文化终于露面了,付文化说:“想死你了,出来见个面吧,朝天阁。”这词是某个相声演员的开口词,付文化的腔调学得挺像,看来他今天心情不错。我正要问问他的近况,他已在那头掐了电话。
朝天阁地址在朝天宫附近,这朝天宫是东宁的一处名胜,如果你有耐心听付文化“讲古”,他能从春秋的冶城讲到元朝的玄妙观,从明朝的朝天宫讲到民国的“首都高等法院”,可以给你讲上几天几夜,让你不得不叹服,人家名字里“文化”这俩字还真不是让人白喊的。朝天阁好像与朝天宫八竿子打得着,却根本不是一回事。朝天阁里有“阁”,但它与朝天宫里的飞云阁、飞霞阁不是一个概念,它就是弄堂里百姓旧居的一个阁楼,拆了四面的木板墙,换成了全透明玻璃,揭了阁楼顶,换成了琉璃瓦飞檐,上为宴厅,下为厨房,对外一天只服务一桌,顾客至少得提前一个礼拜预订,排队等着。付文化以前喜欢在这里待客,价格死贵,吃完最后一道菜,肚子常常还没填饱,我不喜欢这里,太虚,但付文化喜欢,就像他喜欢穿唐装戴腕串一样,他讲究个“文化范”。我一个教古典文学的大学教授,接受不了一个包工头的“文化范”,不知该笑话我还是该笑话他。
付文化已在朝天阁候着,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司机小张,小张也好久没见了。优秀的司机总是跟车形影不离,付文化的座车跟小张一起失踪,至少证明了小张想做个好司机。小张回来了,看样子车也应该回来了。我朝巷口瞥了一眼,那辆奔驰G63真的神气活现泊在那里。付文化说:“豁牙,没想过我有回来的一天吧。”我说:“在付文化身上,发生什么事我都不意外。”付文化穿一件对襟褂子,腕上仍然是串珠,但络腮胡极其茂盛,与鬓发连起来了。以前他都是刮得干干净净,耳根到下巴铁青色。现在蓄了须,人顿时添了几分匪气。我摸了摸他的腰后,疑心他是不是揣着斧头,我在东宁城里第一次与他喝酒,他的后腰揣着板斧,一左一右两把。他笑着扭了扭腰,说:“痒,别闹,都什么年代了,还揣那玩意儿。”我说:“看样子你腰杆子又硬起来了,不需要那东西撑腰了。”小张插嘴说:“那是,周教授,H集团重组了,我们老板的钱要回来了。”
做建筑工程的人,没有不陷入连环债务的。付文化这种包工头出身的建筑公司老总,本来就没有强有力的资本撑腰,竖旗杆时,接个工程就像单身汉娶老婆,全靠左邻右舍凑份子帮忙。凑不齐,那就得赊账。塔吊脚手架可以租,租不到的只能赊。钢筋水泥这样的主材一般是甲供,沙子石子红砖之类得施工队先解决,一幢楼的辅材不是个小数字,好在总有建材商苍蝇一般在工地盯着,他们哭着喊着要把材料赊给你,前提是看到你的中标合同,计算好了合同上的付款时日,拖欠一天就得付利息,生意人比鬼都精明,白纸黑字跟你签合同,工地在,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但指望甲方按时付款,这大多数情况下属于梦想。建材商可以跟你翻脸,大不了下回不跟你做交易,所以他比黄世仁还逼得紧,逼得你恨不得学杨白劳喝盐卤。可甲方你不敢得罪,人家是你的衣食父母,即使你不想接后边的活儿,你早在当下的工程上投下了身家性命,惹人家不高兴,给你拖个一年半载,你这工程队本来就是驾破车,一拖就给拖垮了。怎么说呢,人们只看到老板人前吃肉,看不到老板背后跪舔。在这样的时刻,也会有自称救星的人出现,谁?贷款公司的人。建材公司的推销员跟石子黄沙打交道,在工地脚手架下钻进钻出,戴个安全帽,那模样与工地上的农民工不相上下。贷款公司的人牛气烘烘,西装领带,手里拎个公文包,不跑工地,跑办公室,工地上的老板是幕前角色,幕后老板指定藏在某个办公楼里,哪怕租他也得租个办公室。这种贷款公司的人穿着打扮跟银行员工一个模样,但贷款利息是银行贷款的几倍,说白了人家经营的就是高利贷,在法律允许范围的高额利息。银行利息是低呀,可人家不敢贷钱给你,你这工程队就是个草台班子,人家怕钱打了水漂。那西装领带的人坐在沙发上,偶尔点根烟,喝口茶,时间长了,你隔着办公桌看上去,会把那人看成一个肉饵,明知道那肉里藏着钩子,上钩了你就是一条死鱼,你还是睁着眼睛吞下去了。有多少施工队忙活的工程,利润都交了高利贷,只有工程队的老板们一肚子苦水,自己心知肚明。一旦拿到工程款,首先付清高利贷,几乎是所有欠债人的明智之举。付文化说:“我找邢大贵,可怎么也找不到他了。打电话电话停了,上他公司发现公司关门了。奇怪了,他找我一找一个准,我找他,比大海捞针还难。”邢大贵就是一家贷款公司的老板,这本来是老鹰抓小鸡的游戏,现在反过来小鸡觅老鹰。我说:“你这回是真有钱了,急着还贷?”付文化说:“一天不还掉那钱,我就夜夜睡不着。”他说的是真话,付文化接着说,“你替我打听打听,他是不是在里面了。”
经营高利贷的人,都免不了打些擦边球,比如做出殴打、扣押欠债人这种行为,讨债人进出局子是常有的事。
我应下了,教了三十年书,方方面面都有我的学生。我说:“这些日子,五妹还好吧?付笑笑呢?这小子长久没来我家了。”
付文化说:“好,都好,前一阵都随我住到乡下了。”
我想起他在东宁的另一个牵挂,白马白城湖,它寄养在我一个熟人在江宁的马场,我说:“你有多少日子没去看白城湖了,马想你了,马场场主也念叨你了。”小张又一次插嘴说:“我们去过了,寄养费付清了,又续了三年的钱。”
付文化以前在东宁建筑市场,也属于知名的老总,也有过辉煌的时候。老板们发财后有的养一个歌舞团,有的买一个足球队,付文化在他高光时刻选择了买一匹白马,是一匹,不是一群,不排除这是他财力有限的原因。那匹叫白城湖的白马,即使在他玩失踪的日子,每次打电话给我时,他还不忘记嘱咐我去看马场里的白城湖。
付文化说:“教授,我真的是从内心感谢人民感谢党,要不是把那几个贪官逮了,我那个工程的工程款就不会被清理,再拖下去,我永世不得翻身了。”
看他说话时诚恳的样子,我信。但看他那东山再起的得意相,似乎好了伤疤忘了疼,我忍不住挖苦他,说:“你要感谢,首先得感谢我。没我,你死过几回了。当初,你爬上塔吊跳塔,不是我让大伙抱住你,你现在也只能含笑于九泉。”
付文化说:“你以为我真会跳塔?那就是做个姿态给人看嘛。不说了,不说了,那一页总算翻过去了。”
付文化正色说:“有件事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讲,今天还是向你坦白了。”
我说:“就你?还有什么事情有必要在我面前藏着掖着,你还有什么丑事儿需要瞒我?”
付文化说:“你还记得两年前,我托你一件事,如果有一个叫邢莞尔的学生报考你的研究生,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请你优先考虑她。”
我想起来了,有这么一回事,那时的付文化,已经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事他是在电话里拜托我的。我知道付文化办事的方式,比如说他以前接个工程,那是在还没有招标制度的时代,都由甲方领导说了算。别人都是直接拿下一把手,一把手可以一人拍板。付文化不,付文化做工作分层次,他当然得拿下一把手,但他并不罢休,他会去做基层人员的工作,从相关科员到科长,从相关处长到分管副总,他把工作都做到位,不需要他们挑担子,只要轮到他们说话时替付文化的公司多美言几句。付文化说,至少得让他们觉得,这付文化尊重我,花费多少在其次了。等到开会决定时,一把手只要顺水推舟,既然大家都认为这家公司条件最好,那我尊重大家意见,就这么定了。会议纪要上,一把手的表现极其民主。有这样聪明的乙方,一把手当然高兴,后边的工程还会想到付文化。付文化曾在我面前多次吹嘘他这一套手段,并列举过多个成功个例。付文化说,甲方是我的衣食父母,我不能让领导为难,不能让对我好的朋友为难,为难我自己,那才是应该的。他讲的那个保送生邢莞尔同学,我不知道付文化在前期做了多少工作,反正我看到该生的材料时,她完全符合研究生录取标准,既然她申请做我的学生,有付文化在前打过招呼,邢莞尔就成了我的研究生,现在已读研三。
付文化说:“邢莞尔就是邢大贵的女儿,她或许有她爸爸的消息。”
我明白了,这才是付文化与我见面的目的。我说:“我替你去向她打听一下。”
付文化说:“我一直想当面向你道谢,谢谢你给我面子,收下了这个学生。可这两年的日子,我身不由己,加上疫情的缘故,这事一直拖到今天。”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付文化,咱俩有这必要吗?只是,这么些日子见不着面,我也确实想你了。”
付文化今天的吃相没了斯文相。从一个人的本能吃相能看出他的生活状态,当剥掉了文明或者文化的外衣时,赤裸的付文化才是那个我熟悉的发小。
(节选自2024年第3期《芙蓉》余一鸣的中篇小说《牵一匹马或一朵云》)

余一鸣,中国作协会员,南京作协副主席。曾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花城》《钟山》《作家》《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著有小说作品十六部。曾获2012年人民文学奖,第四、第五、第七届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2011《小说选刊》年度奖,2011《人民文学》年度小说奖,2014《创作与评论》年度小说奖,《北京文学》双年奖,首届高晓声文学奖,叶圣陶教师文学奖,南京文学艺术奖,金陵文学奖等奖项。
来源:《芙蓉》
作者:余一鸣
编辑: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