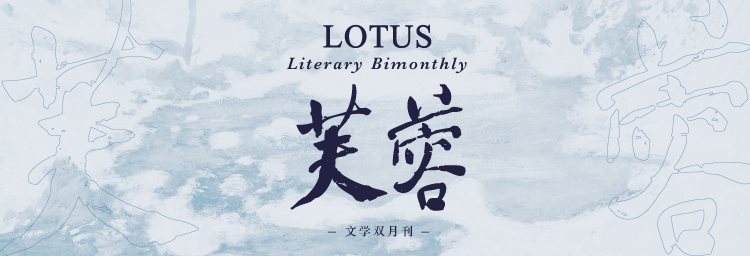

亦如经络
文/习习
1
没人会对痛楚上瘾,但当我看到皮肤上矗立的钢针列队有致,旗杆一样闪着银光,神经质地微微跳动,竟有隐隐的舒爽。就像在酷烈的冰冷中,嬉戏更冰冷的水。
医生说我中了南方的寒气,寒湿锁在身体里散溢不出,故而全身暗疼不止,中医谓之“寒湿凝滞症”。
的确,南方冬天的冰冷阴湿,我已无法忍受。北方虽然寒冷,但冷得干冽爽快。我告诉医生,那地方多雾,终于放晴的一天,去郊外晒太阳,坐在石椅上看书。当时并未觉得很冷,回到住处,觉得里里外外寒透,打开空调,钻进被窝,把自己烘了很久。
医生说,表面热了,但是寒湿钻进了身体的缝隙里。
那些阴湿的寒气会不会就寄居在身体的穴位里?医生每日问我是否还疼,我说疼,他便开始扎针。他好像要用针把那些凝结在穴位里的寒气催逼出来,我感觉他的针刺循序渐进,一天比一天尖锐。我的忍受力也一天比一天强大。
我躺在病床上胡思乱想。人体穴位,会不会像天上的星宿,连点成线,构成不同的经络?连点成线的经络是否如同星座?
双手平放胸上,合谷穴上各矗立一根针,它们对应着远在前方的脚拇指旁站着的两根,像四个卫士,构成一个看不见的四方体,几乎覆盖我的全身,这大概就是个自成系统的经络。那天,医生在我脚拇指的另一侧多扎了一针,这根针显得十分孤立。之前,医生手里悬着针,转头问围成一圈的实习生:“谁能说出这是什么穴位?”没有回应。我竟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但我实在不知它叫什么。医生将针扎入穴位,我的腿条件反射地跳了一下,医生对实习生说:“记住,这叫太白穴。”
穴位的名称听上去很有玄机,比如合谷穴,又叫“虎口”。张大拇指食指,刚好构成一个紧张的虎口。如果人手也可以称为蹼的话,虎口就在活动最自如面积最大的一块蹼肉上,它就在五根手指中的老大身边。想想看,没了老大,别的四根手指将怎么过活?还有脊椎骨上的“命门”,听着就厉害。太白呢,像星宿的名字,单和它连着的穴位便有行间、内庭、太冲、陷谷等,如若仔细追究,大概每个名字都有来头。医生给实习生在病床边讲课时,我也在听。他提到了脚掌中心的涌泉穴,我查了一下,发现那就是人们被挠痒痒后由不得自己大笑不止的地方,我想到一个可笑的词:笑如涌泉。
年轻的实习大夫说,手能通过扎到身体里的针感觉到人体的穴位,如果扎得准,会感觉针尖被吸入一个微妙的旋涡。这样的旋涡在身体上有多少个?他说:“大致361个。”我说:“这不就是一年的天数?”他说:“针灸学的确玄妙。”
2
理疗室里,一位男病人,剃净头发的光头上扎满针,如芒刺林立。他坐在那里,谁都远远躲着,怕碰到那些明晃晃抖抖索索的针。医生开始揉捻,揉捻到不同的针,他发出不同的喊叫,听上去疼痛又凄厉,但我不知这个描述是否准确,或许就像敲击膝盖时的膝跳反射,只不过是不自主的反应。后来,医生给他身上扎针时,他躺在我隔壁床上。他不再发出声音,但过了好久,我听见他呜里哇啦乱叫,我才知他不能说话,陪他的女人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耐心地说:“别急,时间还没到。”
医生看了我的X光片,说我的骶骨有问题,再用紧握的两只拳头放在他的咽喉处,说:“我说术语你不懂,你喉咙后面颈椎上的小骨头结构有些紊乱了。”他把两个紧握的拳头做出错位的样子。
大概就是骶骨上的问题造成我不时腿疼。小时候,走路时,我总能听到腿上的骨头声。晚上,和母亲一起走,骨头声好清晰。我问她:“你能听见我骨头的声音吗?”母亲笑我:“哪里有什么骨头声。”但我听得清楚,咔嗒咔嗒,在左腿大腿根上,就像裤兜里装了什么硬物在磕碰。医生说:“左边骶骨比右边高出一块儿。”他使足力气给我推拿,闪转腾挪,我感觉他已满身是汗,他在用尽手段对付那块高出的骨头。
医生在我骶骨旁的穴位扎针,一针下去,某种难言的感觉倏地传到脚上,似乎是穴位遥相呼应、经络疏通了,这时医生总问:“下去了没有?”我说:“下去了。”没有主语的一问一答,医生和我都明白。医生说,脖颈上针刺的时间不宜长,大概和脑袋相近的缘故。依旧是针头底下倏忽间的传导,像在无形的经络上,那种无名的感觉飞速掠过身体的各个卡口,传达密语、暗送信号。
3
北方的太阳真好,病房里春光荡漾。我的床位是临时加的,有了正常床位后,护士问我是否换床,我说不换了。我的床边无任何辅助设施,没有夜灯,没有摁铃,连贴我名字的地方都没有。别人喊我31床。我喜欢床上洗得很净的旧床单,快要磨破的样子,十分绵软。天气好的时候,太阳能把病房晒大半天,我的床几乎一直沐浴在阳光里。
这里看不到血,看不到楼道里医生护士急迫地奔跑,听不到撕心裂肺的喊叫。除过那些纤细的钢针,这里没有多余的对抗身体的坚硬锋利的东西。
我想起很多年前父亲被车撞伤后住过的医院骨科。不断有骤然拥进的人群,楼道垃圾桶里能看到浸满血的衣服,伤者的喊叫令人毛骨悚然。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焦躁的摁铃声此起彼伏。
父亲临终前进了ICU,我在门口的长椅上彻夜难眠。灯火通明的ICU里的场景令我终生难忘。躺在椅子上,能听到病房深处隐忍的呻吟,像从地底下传来的,深厚、疼痛,我花很久的时间辨别呻吟声是否发自父亲床铺的方位。总在夜半,医生推开门,要我把父亲的各种化验管送到检验室窗口。没有人迹的深夜,灯影光怪陆离,莫名的阴鸷四处漫漶,我跑去跑回。医院是积攒阴冷的地方。还有医院电梯,常常人满为患,父亲和弟弟住院时,我运气好,总能在拐角处找到一部畅行无阻的电梯。后来,病逝的母亲,躺在临时的棺椁里,就在那部拐角的电梯里下了楼。
但在这里,电梯安置得光明正大,依旧人多,但可以敞亮自由地选择。
一天的治疗从扎针开始,然后是艾熏、药包热敷、理疗。这大概才是完整意义的针灸。艾条未点燃前像褐色的炭条,被放进蜂窝煤一样的电炉里,燃着,摆进木盒。
灼艾的热透过木盒底部传导到身体里。最早出现在战国金文里的“艾”字,字形很像两只手放在草下,正像艾熏。普普通通的一样植物,几乎穿过了有记载的中国历史。在西北,万物生发的端午节,它出现在很多人家的门口,被束扎成文静的一把一把,用它深长浓郁特有的气味为人们辟邪祛病。据说,端午这天采的艾,一年里药性最强。我喜欢古人互致平安时用的“艾安”一词,看上去听上去都柔糯安逸。
阳光照着,各种草药,气味弥漫。趴在床上,艾盒就在我的颈部,温热舒适。我几乎要在这温熏中睡着。打开木盒看,烧完的艾条是一尘不染的银灰色,还保持着一根根小柱子的样子,但稍一触碰,它就坍塌为一堆堆细腻干净的灰。
中医就是这样温文尔雅地医治着人,吻合着儒学的中庸和恬淡,隐约神秘、缓慢深长、以柔克刚、里应外合。
(节选自2024年第3期《芙蓉》习习的散文《亦如经络》)

习习,甘肃兰州人。作品刊于《人民文学》《十月》《天涯》《花城》《中国作家》《青年文学》《散文》《美文》《世界文学》等。作品被多家刊物和选本选载。著有文集《浮现》《表达》《流徙》《风吹彻》等。曾获冰心散文奖、三毛散文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甘肃省“黄河文学奖”一等奖等。
来源:《芙蓉》
作者:习习
编辑: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