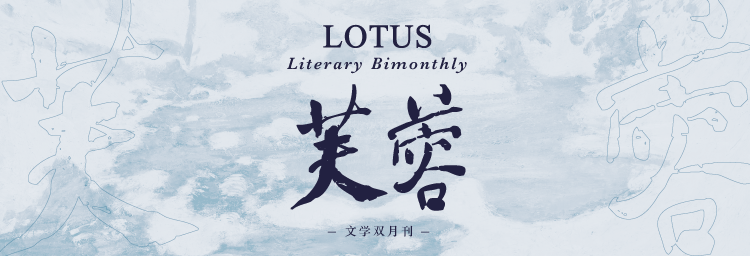

蔡高龙/摄
偶游记
文/胡竹峰
日照兮
很多年没有来过这一方土地了。
日照和暖熨帖,初秋海滨,夏天的燥意缓缓退下去,海水依旧无际无涯,山的气象也苍茫浑厚。想起海风山骨。山风海骨如何?海骨大多一味嶙峋,线条简单又千变万化,又憨又灵,拙稚的朴素中见繁华,有混沌有沉静有动荡。山风干脆坦荡潇洒,让人欢喜。
听过无数次山风,在瓦下,在窗前,在山中。早春的风徐徐吹过,湿润生青的兴发之气荡漾开来。夏日午后,暑气正热,山风化作笙箫,婉转缠绕在一个个山头。深秋偶起大风,松涛呼啸如浪涛拍岸,有海水涨潮的意思。冬天的风,凛冽如刀,一声声跌宕萧索。倘或下了雪,风吹过,山里有佩玉鸣銮之声,像敲响了编钟。
人靠近海或走近山,能焕发生机,泯灭的童心也渐渐复苏。
在日照海边,日色大好,想起做孩子的辰光。暑天午后,大人午睡了,推开侧门,去老房子看阳光下天井中飞舞的微尘,湿气蒸蒸而上,弥漫堂屋四周。靠墙角石基的青苔还是湿润的,青砖上爬得高些的苔藓渐渐委顿。打谷场上几个团筛晒满稻谷,稻穗金黄,阳光也金黄。时间针脚绵密而义无反顾,屋檐的光影缓慢悠长,一寸寸靠近墙壁,一节节倒退。乡村生活自有天地,周旋在屋前屋后,周旋在坛坛罐罐,即便繁忙也舒缓从容。洗洗涮涮、缝缝补补,都是生活的味道。
此地有过一段日子叫莒国。
春秋时,齐襄公专横暴虐,公子小白离国出逃莒国避祸患。很多年后,小白返齐坐上了君位,称齐桓公。有一次,举行盛大的寿宴,鲍叔牙上前祝愿,说不要忘记出奔在莒的艰难岁月。桓公拜谢:寡人与士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则齐国之社稷幸于不殆矣!
谁的人生都有一段在莒的岁月,也需要“勿忘在莒”的情绪。最难熬蹉跎在莒、前后不得,任命运的剑戟一次次穿身而过,无处可躲,躲不胜躲。人生的明箭躲无可躲,人生的暗箭更是不知不觉在黑夜里蓦然而至,防不胜防。
零零星星读过东海之滨的莒国往事,史书泛黄,国家湮灭,臣民不在,只有海与山连绵浩渺。原以为一砖一石建起来的城池坚不可摧,时间之水漫上来,冲洗得无影无踪。光阴无情,何止寸金难买,丈金也买不到。“逝者如斯夫”的声音,从两千年前的川上一直流传至今。
午后有些昏沉,阳光泼辣,大放光明。车行如水,去浮来山定林寺。
甫入山门,一株大银杏树迎面而来,赫然突兀而至。树影塞得眼底满满的,不躲不藏,轰然昂然肃然。第一眼没有看见绿,看见的是褐色的树干与树后的青砖黑瓦,还有团团系住的红丝带,写满世间心事与凡俗愿景。
四五千年的岁月,一棵树立在读书念经声中,立在市井嘈杂中,立在求佛拜祖中,经过无数次风吹日晒、雨雪雷电。一百多万个日夜,草木之躯变成山河湖海,化作铮铮金石。让人疑心它是南山飞来的仙家之物,早已跳出三界。
老树是草木之神,是岁月之神,时间遗忘的沧海遗珠,使人与古代亲近。恍惚里,从三朝到春秋战国,两汉三国的风云依然演义,唐宋明清,一幕幕闪过,都是银杏前身,瞬息而已。山川草木远比一个帝国一个王朝坚固长久。
前人古国荡然无存,植树人当年怎么也想不到这一树苗如此久远。不远处,黄海之水依旧重复过往日日夜夜潮起潮落,带走一盏盏木船的渔火和岸边的灯光。
树干极大,如泥塑如铁铸如铜水浇灌而成。树冠更大,一树绿叶在荫翳里,叶脉苍黄郁绿。站在树下久了,生出沁凉感,伸手不及片叶。不知道是不是岁月久远的缘故,觉得那一树银杏叶也很古老。
有一刹那的懵然,呆呆站立着,一瞬间是一个人的树。每寸树皮每片树叶,都有故事都有心事。树皮苍茫,像旧画的色泽,鼻底隐隐有旧气,是古树的气息,是砖瓦的气息,是墙角苍苔的气息。不自然就怀旧了,想起皖西南乡野的气息,想起年少时光。风吹过,树叶摆动极为缓慢,自在安稳,不以为意又独自沉迷。脑海走马灯似的浮过一幕幕历史故事,身躯被一棵树缠住,心灵也被一棵树缠住。在南方见过太多巨大的榕树,在村口,在山野,让人觉得震撼,却从未被压住。榕树之大,只是旺盛,少了岁月时间的压力,少了投入心灵的重量。
时令秋天,除了傍晚后的潮气与偶尔飘过凉风,四野还是盛夏气象。老银杏一树大绿,绿荫下,一头一身清凉。枝干或伸或曲或虬或折,有一种荒落清寂意思。再过几个月,寒风萧瑟,树叶飘零,那是另一番况味了。
树后有刘勰故居,说是故居实则是校经处。门口对联有话头:法汰东来传禅定,慧地北归校心经。
不知道南朝时候的格局是否也如今日模样。当年的校经人,肉身入土,魂灵大概归于古树了。一本本校过的经书,一代代纳入人心,上善若水的教化天下流传。
校对着古老的经书,仰望古树,叶落春生一年又一年,那时候的刘勰是长袍袈裟裹身的僧人。在清晨午后傍晚的树下,会不会走走看看,看看远处,看看脚下,想一些虚无缥缈的心事呢?
隐逸的人逃离再远,逃不过命运的无情与时局的动荡。狂风暴雨冰雪压住荒草,荒草总有起身的时候,人生不会重来。人如草芥,又不如草芥。刘勰才会说人虽集万物之灵,却像草木一样脆弱,所以要留下文章,名逾金石之坚。这样的感受年纪越大体会越深,实在是因为体悟出人的渺小吧。一世浮埃,念想文章灿烂不灭。
站在大树下,念头是关于回忆的。前些年见过一幅明人手笔,画的也是大树,雨天挂在旧宫殿里,与杜牧、苏东坡、徐渭的笔墨真迹一起。悠悠天地之间只有一棵树,粗壮如屈铁,孤零零的,树叶落尽,枝丫簇簇,一片萧瑟的秋冬残景。天边一抹晚霞,青山隐约如沙丘。身着白袍红衣的老人,持杖徘徊行吟,站立土坡遥遥远望,像是不忍离去,又像是无奈作别。那一幅旷远的图纸,困囿了太多鲜活的生命。
纸本古树背景简练空旷,飘零罄尽,却有傲然不屈服的倔强,绝去甜俗蹊径,是董其昌所说的士气。听之有声,思之成咏,给人沉郁、悲愤、孤寂、苍凉之感。作画者自题有七言绝句:
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西山四海孤。
短策且随同旦莫,不堪回首望菰蒲。
诗里情绪太多,逸民难掩的苦楚,史家孤愤的心事。书上说,清军攻陷嘉兴城,画家外逃避难,家里遭劫,半生经营半为践踏,半为灰烬。堂兄不愿降清,带着两个儿子和一妾跳水自杀。万物如烟云过眼观之即可,身在其中,谁又能逃脱哀愁。肉身易碎,有些人的气节却从来压不垮,寓于文字,寄于丹青墨迹,心性难熄的火种藏在炭灰里。
题画诗鲁迅多次书录条幅送给友人,说忘何人所作,将原文“日薄”易为“日落”,“西山”改换“沧溟”,“短策”写成“杖策”。那是前辈玲珑的文心与跌宕的机巧,也是字里游戏。
画家崇祯元年曾经齐鲁,出长城,历燕山,游妫川,一路走走停停九个月。不知道作画人有没有踏过我今日走过的土地,来到眼前这棵大银杏树下。姑且当他来过,姑且将那一幅纸本大树当作写生图页。生和死、古与今、虚或者实从来须臾不分。
在齐鲁大地行走,脚下土地有最初的日色,也有中华文明的曙光。古书上说这一带人天性柔顺、好让不争,故能礼让处世,宽大宽容,也就是俗话说的有容乃大。心想也只有这一方土地能容下这么大这么老的树。
大树多长在万木葱茏、花草杂陈的地方。人也如此,要做自己的树,又不能脱离人海,与世无关又唇齿相连,陶渊明离群索居也还有他的酒客。
安静的夜晚。真是安静的夜晚,不安静又如何?或坐或卧于灯下,闲翻一本本旧书,有册《文心雕龙》。“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起句口气之大,气势恢宏,也是仕途舛逆后的慰藉。文心是言为文章的用心,刘勰的文心以惆怅喂养而成,如青铜古物,在命运起伏与静寂里掩埋长久,出土时已经生满了铜绿。
刘勰观物体情细腻到让人惊喜,偶有诙谐。书上说,“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到底太多不甘,凝成奇崛的玄学与偏激的论点。那时候的刘勰未经不惑,年轻的血性在时代与命运的压迫中一点点回流,化为文字,自笔管流淌而下。
当年劳神劳力中,靠一本本书吊着一口文气不散,《文心雕龙》更是一章章看,对灯而读,一字一句不忍错过。书末诗赞掷地有声∶
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
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太阳是天上的日头,文字是地上的日头。太阳光照生发万物,文字的光照打亮人心。倘或没有文字,万古真像漫漫长夜一样漆黑沉闷了。文字虽迥异,却记录了不同人种的光明,让生命焕发出光彩。
刘勰家贫好学,郁郁不得志,以字为业,一生志趣信仰如此,有浩然气。实在也是无奈,最后不得不烧发明志出家为僧。据说他晚年自建康还籍,在浮来山营造北定林寺,最终蜷缩在山野古寺老树下。古典悠长的浪漫背后有太多的无奈凄清。
《文心雕龙》之外,看过刘勰老来给石城寺石像写的碑记,经冬银杏的况味,别有情愫。老来一味为文而文,少了天朗气清的贵气,没有《文心雕龙》跳脱自喜。倒是清人赵之谦留下大楷墨迹碑记存世,苍劲有力。
踏出石阶,太阳斜挂西边,照过那一座我不知道名字的山脉。峰峦在苍茫里蜿蜒而来又蜿蜒而去,不知首尾。黄昏落日下,反复想起那幅纸本树,想起那棵老银杏。回头看看,空无一人,几声秋蝉微弱的鸣叫,几声鸟鸣。日暮途远,一时忘了人间何世。树下好像立着一人,长髻古服,举头仰望,远处是落日。日照之下,万木淡淡金黄。
日照,日出初光先照。日照,灿烂日光映照。是幻觉,也可能是天气太热,日照之下泛着白光,尤其是远山的石头。草木是浅色的绿,衬得石头格外白,像匍匐着一尊尊玉麒麟。日照灿烂,天空晴朗。
那几天贪睡,真该去海边看一次日出,东方大地曙光先照的日出,是一幅恢宏的画。想起另外一幅纸本山水,高山大岭,白雪皑皑,长城逶迤起伏,苍苍莽莽的黄河奔流不息,大海波涛滚滚。云开雪霁,画面一轮旭日金光灿烂。日照兮,日照兮,照出欣欣生气。
走洲
和悦洲的名字好。和,和气和谐和煦和暖,祥和柔和温和。悦,喜悦欢悦怡悦。新年出行,找个好地方,兆头好,让笔顺一点。写作是谋生的手段,文人难当,腰无万贯家私,腹内漆黑一团,不知道才高几何,凡事得讲究些个。
友人去采风,准备写本新书。我纯粹玩玩,打秋风的。时令是春天,打春风吧,秋风萧瑟,干瘦瘦的,不实惠。晚饭吃到野生甲鱼,果然比秋风实惠。
和悦洲四面环水呈圆形,似荷叶漂浮水上,原名“荷叶洲”,历来是商埠重地。生意人讲究吉利,遂改名“和悦洲”,和气生财。
第二天到处转转,拐弯,再拐弯,路边有水,初春的气息从窗外挤进来。看见一座寺庙,山门开阔,一僧人走出来接我们。庙里一些题匾,书法甚好。
在寺里转了片刻,去老师太静室喝茶聊天。老师太神色平静,修行了一辈子的人,气息与凡俗不同。
出寺后去天主教堂的遗址看了看,只剩下一个大门。破败比完美好,尤其是古建筑,翻新的亭台楼阁远不如一地瓦砾耐人寻味。和悦洲上的破墙残垣是时间散落的一地碎片。
在小镇走走,感觉十分有烟火气息。
街边不少卖菜人,摆一张木桌子,或者放在挑子里,有人索性把菜摊在地上。芫荽,茼蒿,野芹,鸡鸭鱼肉。回家时,带了一条干枯的丝瓜,准备请画家焦墨写生一幅,题上“今年树上挂着去年的丝瓜”。同行的人是黄复彩、张亚峰、魏振强。
青翠碧绿一段滋味
四点左右到千岛湖,第三次来浙江。浙江我去得少,渐江倒读得熟。这些年经常足不出户,大把时间在家中打发。在车上一边张望,一边伸懒腰,眼前的景色有点渐江画意。有论者云渐江书画“墨如烟海、境界宽阔”,千岛湖也差不多这样。
前几天读完渐江《山水册页》,让人大有好感,笔法随意,墨色自然,又难得天真与酣饱。天真里有饱满,婴儿的一团元气;饱满里有天真,老人的一派和气。
第一次来千岛湖。岛不稀奇,湖不稀奇,千岛之湖稀奇。我对千岛湖是有些向往的,与其说是对千岛湖的向往,不如说是对山水的沉迷。
太阳已经挂斜,贴在西天,悬而未决,蹭在那里,迟迟不肯下山。远处的水一片橙黄,如风吹稻田,脚下的湖碧绿旖旎,像雨打麦浪。
绿水春犹在,红湖夜未临。
独立西风里,无雨亦无晴。
面对一片好山好水,想酝酿出一点文学的感觉,散文难写,旧诗好作。好作也只能作出四句。古风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写散文是我的饭碗,诗歌属于天才,我知道自己不是。
去过不少江南小镇,千岛湖却是大埠,非常城市化。汽车走街串巷,与所见的城市没什么不同,差一点大失所望。看看远处的湖水,心头的快意稍微多了几分。
去过的江南小镇,一律小巧、古拙,一段朴素的世俗生活历史,千岛湖不是。千岛湖太大,又太嫩,没有历史,没有人文,只有自然景观的可观。历史是岁月的沉淀,引人怀旧,人文也能让人遐想。自然景观之美,美得直接、美得单纯、美得本色,像毫无心机的少女,水做的骨肉,有成熟妇人所无的活泼与真实。
入夜下了雨。南方的雨带着凉意,这凉,凉得轻薄,敞头出去走走,轻靡的雨薄薄地洒了一身。走不多时,雨势渐大,只得返回。打开窗子,嗑瓜子,等着睡意。瓜子快吃完了,睡意不来夜过半,实在没耐心了。洗澡刷牙钻进被窝,枕雨而眠,恍恍惚惚听见大雨扑窗。
平日里没事,喜欢睡懒觉。出门在外,有一帮同游者,只得早起。昨晚睡得颇好,比昨晚睡眠更好的是今晨的早餐。我吃了八分饱,剩下两分是惦记。
千岛湖的早晨很安静,抑或下雨的缘故。几个原住民模样的人不时在路边走过。游客都有目的性,那几个人无所事事的,悠闲中有一点自负,自负中有一些敌意,应该是原住民。对他们而言,我们是不速之客。
时间过得真慢,透过玻璃窗听见雨滴打在伞上慢吞吞的声音。时间过得真慢,慢得能听见雨伞上水珠落在地上的声音。时间过得慢是因为同行的两个女人起得太迟,足足让大家等了半个钟头。
好不容易出门了,街头空气清爽,皮肤像刚洗完澡般湿润,地面积了很多雨水。进了湖区,雨声淅沥,水面烟波浩渺。一座座小岛缓缓在船畔流过,那些岛临水萧散,一副悠闲自在的模样。
游山玩水,山要走,水要玩,把玩的玩,最好乘舟划桨,方有意趣。可惜我们坐的是游轮,如果是小舟,一边摇橹划桨,一边东游西荡,体会着青翠碧绿一段滋味。船上有人谈情说爱,我掏出昨天买的酥饼,慢慢吃,他们男女,我饮食。饮食男女,各得其乐。
站在船舷仰望,一只不知名的水鸟从头顶飞过。
西庐寺
紫蓬山的名字好,紫气蓬莱,有仙气。西庐寺的名字也好,有隐士气。陆游说青山可结庐,“结庐”二字入了不少他的诗:结庐云水间,手斸云根结草庐,晚爱烟波结草庐,结庐城南十里近,濯锦江头已结庐,莫笑结庐鱼稻乡,结庐归占水云乡……
这几天读《剑南诗稿》,一见西庐寺,隐隐生了亲近之心。即便不读陆游的诗,一见西庐寺,也会有亲近之心,因为西庐寺多树,那树古,尤让人喜欢。草要新,欣欣青草才有喜气元气。树要古,不少乡俗以古树为神。古树藏了精气,那精气里静气重,静气一重则平生肃穆。肃穆是大境界,不由人不敬。
西庐寺颇大,紫蓬山更大,故显得寺小了。入得山门,到处是麻栎,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那么大的麻栎。人皆惊奇,惊奇毕了,开始赞叹,赞叹后复生亲近之心。古树苍枝满寺内,啧啧称奇这树不是因寺而长,此寺却因树而建。
树在寺内随便长着,三三两两或斜倾或挺立,亭亭如盖。间有老死者,树桩粗且壮,呈灰褐色。
在寺内走走停停,恍惚中觉得此地是我前世修行之一所在。
自合肥出城去西庐寺,一路雨声风声,雨忽下忽停,下下停停。到西庐寺时已经黄昏,天却晴了,云白天青,朗朗半月在头顶,惹得人欲攀树邀月揽玩。雨后的缘故,傍晚的西庐寺,无丝毫浊气。
西庐寺为皖中名刹,始于汉末。
胡竹峰玩寺,不求佛求圣,只为遣怀修性也。
登秀峰塔记
东流晋时属彭泽县,毗邻长江之南,取“大江曲折来,到此如东流”的意思。陶渊明任县令时,偏爱东流黄菊,常常日驻彭泽,夜宿东流。今人慕其风节,建有陶公祠。
东流古街,历经兵祸水厄,年久失修,很多房子已成断壁残垣。走在古街上,是不动声色的时光的老去。时光让人间的一切付诸东流。
老宅窗下一狗静卧,街角一株盆景迎风而立,弹棉花的铺子里生机蓬勃,发出点声响,其他皆倦怠慵懒,只等着太阳西去。太阳拉长老屋的影子,在街面的青石板上留下刻度。光阴的刻度,此刻,因为古街,仿佛停顿。
秀峰塔建在陶公祠后面的草地上。
塔名秀峰,山清水秀。山偶尔也能秀,江南很多山是秀色可餐的尤物。“秀峰”两字与我有缘,有夸我漂亮的意思。近年越来越不爱照镜子,因为越来越不漂亮,肉身沉重,浊气上行。民国某年九月,郁达夫去苏州游玩,路上遇见一群少女,“把她们偷看了几眼,心里又长叹了一声:‘啊啊!容颜要美,年纪要轻,更要有钱!’”我容颜不美,年纪不轻,也没什么钱。
塔阶极窄,仅容一身。登上塔顶,透过塔窗看窗外,风很大,我站住不动,让东流的风吹着。
杜甫草堂
飞机降落成都的时候,颠得厉害,仿佛诗人的命运。诗人的命运总是颠沛流离。颠沛流离是诗歌的底色,姑妄言之。诗穷而后工,并不见得。过去身无分文,并没能写下半句好诗,倒是炼出一身傲骨。
去杜甫草堂,司机绕了个大弯。去看诗人,绕绕也好,这才是本色。这年头,本色是稀罕物。行人不多,真是难得。游人不少,真是难得。大家都来陪诗人过中秋节。
门票六十块钱,不算便宜。杜甫草堂的理想状态,在我看来,白天是园林式博物馆、艺术馆,晚上是私房菜馆、酒吧、茶楼集聚地,吹拉弹唱,吃吃喝喝。诗人、散文家、小说家一律半价,新闻人、出版商八折,儿童文学家免进,少儿不宜,报告文学家免进,此处无须报告,禁止大声喧哗。
杜甫写过一些关于中秋的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我嫌其大白话,不喜欢,一首《月夜》经常揣摩把玩: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我不喜欢李白,他是天才,不是人,几乎不带人情味。“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这样的句子他就写不出。如果说李白是孩童,杜甫则是家长。少年时偏爱李白,现今喜欢杜甫。杜甫像个老实本分的读书人,读他的诗文,感觉是与敦厚朴素的老朋友面谈。
杜甫草堂的植被很好,旧建筑与苍绿搭配,入眼舒服,仿佛古装少年。旧建筑像古装,苍绿像少年。古装少年好看,古装老翁暮气沉沉,一脸酱色。当然,这是我的偏见,有朋友就认为老人穿上古装才熨帖才端正。
秋天的成都,一个人走在杜甫草堂苍郁的暮色里。前几天还热,今天刚好下雨,气息清爽了。林荫道上隐隐约约幽凉游离似线装书里的蠹鱼。
草堂草不多,树不少。站在杜家门口,庭前大树一头绿叶。在树下放张桌子,喝喝茶,晒晒太阳,吹吹风,站在那里也是好的。
杜甫家的房子,我很喜欢,泥墙中有草有竹,唐朝的房子差不多就是这样吧。虽说眼前的草堂是后来修葺的,过去的格局还在,古人的日常差不多那样。
站在杜甫书房门口,想入非非,认为此处真是宝地。站在杜甫家的厨房,脑子里又狐疑当年诗人会不会在灶下添柴生火。
杜甫的诗读过不少,棱角峥嵘,一脸忧患。他在成都草堂几年来写下的作品,心境颇好,到底岁月安定。
十来岁的时候,读到杜甫的诗,像在亲戚家拜年。二十年过去,每每读到杜甫的诗,还是感觉像在亲戚家拜年。杜甫的诗是土豆烧牛肉,又解馋又充饥。杜甫的诗歌是庙堂式语言迷宫。
现在不大喜欢诗了。诗言志,无志可言。无志青年,写诗做什么?无志青年,读诗做什么?很多年没读过杜甫了。
花是主人
洛阳,千唐志斋。黑的墓志,一方又一方。金戈铁马,骑驴看花。不知人从何而来,却知终归何处。
“谁非过客,花是主人。”这八个字张钫先生所言,刻在石屋书房门侧,书房名为“听香读画之室”。“听香读画”四字是我前生之志今生之志来生之志。张宗子云:“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胡竹峰道:人无志不可与交,以其无心性也。
谁非过客,听香读画。
一山一水
山间的雾,一层又一层,树浓浓裹起来了,人浓浓裹起来了。对面人睫毛上挂着水丝,的确是水丝,像清晨被露珠打湿的蛛网。眼里一幅烟雨水墨,大自然鬼斧神工啊。
脸湿湿的,却有热意。掀开茶碗的盖子,淡香袅袅而上,面颊一暖,怎么写起茶来了?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喝过的天柱剑毫。
怎样的一段光景?是春朝,还是夏时?是秋凉,还是冬晨?我忘了,嫩绿的颜色却记得清楚。嫩绿的剑戟林立,春来江水绿如蓝,春来茶水绿如蓝?不,茶水还是绿的,绿茶之色,绿得明媚而高贵,透明与干净,古典与可人,天然一段绿,落在茶园,落进深山,落进采茶少女的手中,落进制茶师傅的锅底。
有一杯茶在手,多幸福啊。
比杯茶在手更幸福的是有大片茶林。
想象茶林长在山上,融入弥天大雾中,像个弥天大谎,仿佛不是真的。
我突然觉得天柱山的另外一个名字——皖山,更有意思些。皖山是个象征,其文字间带来的历史旧味更能传达一方水土的精气神。如果是秋天,秋风吹落叶,落叶满皖山,那场景,就在山脚下看看,也足以令人低回。
我喜欢天柱山上的石头超过了云海瀑布,甚至超过鸟鸣松涛。天柱山的石头有老态,但老态不过是鹤发,骨子里还是年轻的,也就是鹤发童颜。那些石头落落寡欢地沉寂在山上,分明还有一颗勃勃之心,有些像晚年的张恨水,病榻上依旧孜孜不倦于写作。或许可以换一个说法,著作等身功成名就的张恨水到老未脱文学青年的向上之心。
我以前特别害怕文学青年这个说法,感到难为情,现在觉得做一个文学青年挺好。文学是青年的事业,以青年为业,不知老之将至。
那天从山上下来,去三祖寺的路上,我闻到了满山的映山红之香。
映山红是无味的,可我偏偏闻到了它们开花的气息,实在,是嗅到了春浓的气息,它们开在天柱山脚下,花蕊已经透出腮红般的花苞。人面映山红,似开未开之际的花朵仿佛羞涩的少女。
天天处处多山,一个叫潜山的地方有天柱山。天柱山,一柱擎天,如何潜哉?天下处处有水,但张恨水独一无二,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水长东,惆怅了多少张恨水。
一山,天柱山。一水,张恨水。
没经历的人,读谁谁谁。有经历的人,读张恨水。游天柱山,读张恨水,可谓之游山玩水。倘或把天柱山比作张恨水的话,石牛古洞是《春明外史》,神秘谷是《金粉世家》,天柱峰是《啼笑因缘》,飞来石是《山窗小品》。在天柱山游玩,竟有扑面文气。
游天柱山如清风梦忆。如果记得没错,我读到张恨水的第一本书是《傲霜花》。
南部记
这几天合肥雾霾肆虐,让人生了逃离之心,逃向哪里?雾霾深似海,四顾心茫然。今天晚上想起秋天时去过的南部县,空气清洁,心生南行的冲动。
南部的名字很好,因为南部,让人觉得尊贵。古人视南为尊,宫殿和庙宇都朝向正南,帝王的座位都是朝南,当上皇帝是“南面称尊”。我老家乡下,有句俗话叫“坐北朝南屋,享尽天下人间福”。这人间福是清福,坐北朝南的房子,冬暖夏凉。夏天有清凉之趣,冬天得负暄之乐。
南部,现在是记忆之城与想象之城。上个月在那里东走西顾,吃吃喝喝,眺望着桂花飘香的大路。可惜不喝酒,不然花香的南部记忆里还有酒香的片段。
南部是缠绵的,缠绵中有热烈。不知道是不是桂花之香的缘故,夜访桂园之际,竟有写诗的冲动,那些桂花之香应该围绕着纶巾羽扇的诗人。边走边看,因为夜行,看也看不出什么。看花不如闻花,闻比看格调高,就这样很好。桂花香得富贵,香得内敛,应该穿一身长袍马褂才对得起这暗夜里的锦绣之香。
桂花之香是锦绣的,恰恰古时蜀锦盛名,一时间心生怀古。我好怀古,因为近视,古总也怀得不远,每每在晚清民国徘徊。这一次在南部,一下子起了怀唐宋之古,怀上古之古。唐宋之古与上古之古都是因为禹迹山。
禹迹山因大禹治水留下足迹而名,大禹胜迹至今犹存。大禹的身影早已经走远了,远成了天边鸿雁一声依稀可辨的鸣叫。“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差不多就是这样。空山找不到大禹的踪迹了,大禹的传说却声声在耳。
在禹迹山看看绿树,听听松涛。如果说大禹是久远的记忆,禹迹山上刻凿于唐末的大佛,却是真实的存在。石刻圆雕之佛立在那里,仪态端庄,有唐朝盛世神韵。
见过一些唐朝的佛像。唐朝佛像的代表作应该是龙门石窟吧。龙门石窟的佛像和云冈石窟的佛像差别很大。我看禹迹山的佛像接近唐朝佛像的感觉,面相饱满,大耳下垂,神采稳重而又不失慈祥。
大佛的后面石崖有条秘道。
禹迹山寨是四川境内至今保存规模最大和最完整的古代军事防御工事体系。山是一座堡,山之堡。堡是一座山,堡之山。
历史需要细节,历史才会动人。历史需要遗迹,历史才能摆脱传说的阴影。
禹迹山寨的古堡秘道像一本唐人碑帖,漫漶却让我实实在在嗅到了旧时气息,或者说看见了旧时月色。旧时月色下金戈铁马静悄悄。
小时候读唐诗,读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时,才喜欢上边疆诗的。躬身在禹迹山的古石道中,一下子勾起了唐诗的气味,秦时明月啊,汉时关啊,欲罢不能。当地人告诉我,这些石窟开凿于嘉庆年间,感觉来了,思绪一下子就跳到了秦汉的天空,止也止不住。
很奇怪,在禹迹山游玩的时候,心里有看唐风的感觉,或许因为大佛的缘故。大佛身上的唐朝气息让一座山都弥漫了唐朝气息。
唐朝气息是一种怎样的气息?大气、磅礴、雍容、华丽、端庄,都有一些。欧阳询的小楷,褚遂良的行书,颜筋柳骨,“画圣”的吴带当风,都是唐朝的气息。
我说不清唐朝气息,在禹迹山我又分明遇上了。可惜太匆忙,没好好看看。
南部是四川南充市所辖的一个县,我今天晚上想起来了。想起南部,身在北方,格外想念南方。南方绿色葱郁,让我有南行的冲动。
游青藤书屋记
左拐拐右拐拐,右拐拐左拐拐。一段剥落的粉墙上看到“青藤书屋”字样,灰色的院墙,几枝春绿探头无语。
院不大,一条卵石小径直达阶前。院内有石榴一株、葡萄一架、幽篁一丛、芭蕉数棵、湖石几方、石匾一块,上篆“自在岩”三字。
卵石小径的尽头有一圆洞门墙,门外有井,门内筑池,方不盈丈,不溢不涸。徐渭曾书“天汉分源”四字,以示此水自天上银河来。池边墙根有古木一棵,墙角有青藤一架。藤下壁间嵌有“漱藤阿”隶书石碑。徐渭有诗记此老藤:
吾年十岁栽青藤,乃今稀年花甲藤。
写图写藤寿吾寿,他年吾古不朽藤。
一直想写篇关于徐渭的文章,机缘不到,先看看旧居也好。
登上了长城
此时此地,如果有雪,是有意思的。雪正在下或者已经停了,雪落长城或者雪盖长城,都是有意思的。墙头一片雪中,有墨色,有留白。倘或雪开始融化,大块的黑衬着大块的白,更有意思。
秋日无雪,秋阳似霜。
来京十余次,今日初登长城。上得城头,或远望,或近观,若有思,若无思。城已易砖易石,山也易树易草,登临客易了一天天一年年无数。
残垣废台极美,美在沧桑上。枯荣盛衰,城有了生命。长城如龙,山起则龙升,山落则龙降,往复盘旋如藤架,不知其首不知其尾,或无首无尾耶。人在城墙上,又在城墙下。城墙在山之外,山在城墙之外。
山在城墙上,城墙又在山上。山是城墙,城墙也是山。攀登时一步步数着脚下的台阶,不多时眼乱如麻,于是重数,数不胜数,眼乱心也乱,只得作罢。
走过一座烽火台,又走过一座烽火台,觉得那楼台近在眼底,上得前来,前方又见一烽火台,一座连一座,不知何处是尽头。呆坐良久,思忖并无尽头。忽然解脱,下山吃午饭去也。
游兴
去颐和园。游园之美,只在闲情。皇家并无闲情,游皇家园林也难得闲情。于是上山——万寿山。树下清凉,山气与水汽一体,空明温润,靠树解衣而坐,得自在心。此山名万寿,山有万寿,园林不得万寿,人更不得万寿。一万年后,此园不在,此世不在,山安在,水安在,我不知也,但知二〇一八年五月八日之行,游兴不浅。
夜行杨家岭
夜宿延安杨家岭外客舍,小寐忽醒,再无睡意,忽起闲情。与友人一路漫步,行止无法。风吹树叶,天际微澜,不知屋影山影。几点灯火暗淡,帘前一胖大妇人对镜梳洗。昔日一众聚啸于此,吃小米饭穿粗布衣打天下,真是大闲情。今夜我二人游荡,可谓小闲情。人生苦短,有闲情不易。乌灯瞎火,寻杨兆墓不遇,摸黑而归。
大孤寂
秋日去司空山,夜行回客舍。夜气上来了,雾气上来了,夜气与雾气莫辨。月也上来了,肥硕丰满的一轮月,挂在山顶。
月夜看山只有剪影,那剪影巨大莫名,笼罩前方。山风微凉,吹来秋草枯萎的气息,吹来白菜萝卜的气息。几声鸡鸣自农舍而出,忽然觉得孤寂。一百年的孤寂,一千年的孤寂,一万年的孤寂,亿万年的孤寂。沧海桑田,人生刹那,山影与月影不老。
迷雾
遇见了极好的雾。雾似迷,迷如雾,迷雾也是雾迷。人在雾中行走,迷蒙中不知来路不识去路,随脚而行,觉得处处都是路。山间松姿或虬虬或曲曲,长短浓淡不一,自有仙风,峰岚隐隐如莲花圣地。先闻人语,再见人影,近看彼此眉眼皆有露雾意,不禁相顾一笑。
游冶父山
山下有庙,构建极大。阳光照过,屋顶若流金。一路多是杉树,高且直,遮阴无数,山气清凉。佛音在耳畔响之不绝,鸟鸣清幽,天色向晚,暮气上来了,内心越发清凉。徐徐而行,隐隐有人语。灌木枝叶微动,疑心林深处会走出三五个古人,是仙翁是好汉是侠士是樵夫。据说此地曾是先秦欧冶子炼剑之所在,今山顶有铸剑池。池水清冷,黄昏中凛凛似有剑气。绕池一圈,心想人生亦如刀剑,来一世必得经一世的熔炉火炼。人间诋毁诽谤亦如敲凿锤打,却让顽铁现出剑性。一时欣然,欢喜别过。

胡竹峰,1984年生于岳西,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雪天的书》《竹简精神》《茶书》《空杯集》《墨团花册》《衣饭书》《豆绿与美人霁》《旧味》《不知味集》《民国的腔调》《击缶歌》等作品。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中国文章》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部分作品被翻译成日语、英语、俄语、意大利语。
来源:《芙蓉》
作者:胡竹峰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