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旗渠,不可复制的精神坐标
文/方欣来
一
下午二点从安阳下高铁。虽已近寒冬,漫天洒落的阳光依旧和煦而温暖,我坐上了去林州的汽车。隔着车窗一望,太行山以不折不扣的速度闯入我的视线,那种呼啸而来、绵延不绝却又刀砍斧削般的姿势,让人震惊。古人说的“高山峨峨兮”,大约就是这个样子吧。
此行的目的地是红旗渠,只是我对它比较陌生,在车上用手机百度了下,得到一些信息:位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的林州,在历史上属严重缺水区。从明朝正统元年到新中国成立的514年里,连续发生大旱灾100多次,粮食绝收30多次。想想,那是个怎样境况?瞬间,我的眼睛里闪现出龟裂的田土、枯黄的败叶、奄奄一息的呻吟和一股股随风而起的黄尘。仿佛,偌大的土地上,疯长着浓得化不开的苦难。“易子而食”,这怵目惊心的词语,谁真正掂量过其中的重量?
汽车在高速路上疾驰,两旁掠过的城镇和乡村静谧地站在时空里,连风也夹杂着温和的气味,似乎看不出一点先前的痕迹。倒是,沿途标志牌上的村庄名字颇有意思:李家井、张家池、杨家泊什么的,看起来,好像都与水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更有意思的是,听说这里的庄户人家把他们的女儿唤做水莲、水荷、水蓉的。男孩呢,大都叫什么来水,水生,水根等等,那些名字充满太多水的气息。刹那间,一股与水有关的气味向我扑来。不由暗想,这貌似江南的土地上到底隐藏着多少不可知的经历?是否在时间里经过一番苦苦挣扎后才得以涅槃新生?
二
毕竟时序已入深冬,四面而来的风有些薄凉,路边的池塘里结出了冰,还有不少树枝上挂着冰条儿。阳光照在上面,显得那么干净、湿润,有一种晶莹剔透的美。爬过一个长坡,再踏上一座桥,我的视线顿时被一条宽大的水腰带给打湿了,一旁的碑文用一组阿拉伯数字告诉我:这是一条宽8米、墙高4.3米、纵坡为1/8000的水渠,在建国初期花了整整10年时间,并完全靠人力打造而成的大型水利工程。
那是个特殊的年代,靠赤手空拳在天地间创造一个个奇迹。就拿这红旗渠来说,让水穿过时空,在崇山峻岭之间迂回、流淌,他们把千百年来的生命煎熬和一代代人的梦想,化作无法想象的力量,一股脑儿泼洒在这山山岭岭之间,把他们的意志写在眼前这条“人工天河”上。红旗渠水在险峻的沟渠里生生不息地流淌,流得从容舒缓,不事张扬,恍若把许多时间带走了,又像把无数个日子的味道沉入其中。
吁了口长气后,我一路往前走,终于在红旗渠纪念馆里的一幅图片前停下来:几间破烂茅屋,幽暗、干燥的气息不停起落,有个老汉跪着,双眼朝天,两只手向上高高举着,像另一种形式的“天问”,而天空一言不发,用沉默应对着人间。领队老师却说这是真人真事:当时林县有一个村子叫桑耳庄村,他们每天要跑八里路到一个叫黄崖泉的地方挑水吃。其中有个年过六十的老汉叫桑林茂,在那年的大年三十,一早爬上黄崖泉,挑水的队伍业已排成长龙,轮到他时已近下午,好不容易装满了水,又慢慢探着脚儿往回走,刚进村口天便黑下来,恰好刚过门的新媳妇打着灯笼来接老人,顺手将担子接了。万万没想到,脚一加快,被一块石头绊倒,轰,两桶水泼了精光。媳妇儿慌成一团,老公爹却发疯一样扔掉灯笼趴在地上,拼命把水捧回桶里。你想,泼出的水还收得回吗?那时,他家的年关,冷火秋烟,四下里,只有一波一波的寒风和比寒风还冰冷的惆怅填满屋子。更出人意料的是,那新媳妇羞愧得紧,一根绳子上吊自尽了。大年初一,葬了儿媳,桑林茂一家冒着风雪踏上逃荒之路。“太行山上水贵油,谁知人间几多愁?三尺白绫无情剑,屈斩芳龄少妇头”,这是写给大地的祭辞,还是带血的心灵表达?
三
时光倒流至上世纪1959年,林县又遇到前所未有的干旱。境内河流断流,几乎无水可饮,无水可用。或许,人们又在心里默默念叨:睁开眼看看吧,老天。想必,这样的话语砸在泥土上,准会溅起一串尘雾;砸在石头上,也让石头感觉到疼痛。是的,是痛,像钢针扎在胸口那般的疼痛。时任县委书记杨贵望了下天空,顷刻,被垂直而降的阳光照花了眼。那期间,真个是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下。树挪死,人挪活。也许,这话起了作用,他还真带着一班人马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寻水源。然而,任凭他们的足迹踏遍全县的弯弯角角,给他们的仍是失望与失落。他仰望天空,只有云朵在飘;又俯视一下身边的土地,全在炽日里大口喘气。问天问地问阳光,这救命之水在哪里呢?
那天上午,他在办公室挂着的行政区划地图上瞄来瞄去,忽然眼睛一亮,把目光锁定在境外的浊漳河。恍惚间,那汪清亮亮的水顺着他的视线和思绪,哗哗啦啦流过层峦叠嶂,然后流向千家万户,不一会儿,每个庄户人家的瓦屋上冒出了炊烟。于是,一个“引漳入林”的计划大胆出笼了。当然,这计划的出台,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水利建设,功在千秋,利在当下。这话谁都会说。可是,这项工程偏偏卡在1960年2月这个时间点上,也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年大灾时期。那时节,林县一穷二白,物资十分匮乏,但唯一的条件是不缺少劳力。自然,27岁的杨贵书记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抱定了“高举红旗前进”的信念,不把浊漳河的水引到林县来誓不为人,并坚决把一面面红旗插遍整个水渠。或许,这就是“红旗渠”的由来吧。
动工开始,大家伙劲头十足,好比一只只猛虎下山。天空下,锄头的咣当声、钢钎的斫斫声、脚步的移动声以及大口的呼吸声,与轰隆隆的爆破声交汇、重叠,一座沉睡很久的大山被惊醒了。但世上的事情远不是光有热情就够了。回忆起当年的场景,领队老师认真地说,当初县委对工程的艰巨性和给周边村民所带来的影响考虑不够,认为摆上7万劳力,每人1米,2月初动工,至多3个月就能完工。结果并非这样,开工没多久便发现,把近4万劳力往水渠的沿线一摆,竟看不到有多少人。不单是劳力、技术人员分散,就连炸炮也是乱搞的。轰,这里一炮。轰,那里一炮。满山都是炮响,更麻烦的是,有的人挖错渠线,有的人炸坏渠底……尤其是邻近山西那里的群众意见不小,都说是“白天夜里只听见炮响,碎石、土坷垃满天飞,把不少树、瓦砸坏了,还把一些牲口吓得乱跑,连房子也被震裂”。想想,照这样下去,成吗?这么浩大的水利工程,必须要打持久战才行。
老师说得很诚恳,全是掏心窝子的话。便想,我从事的是公路工作,经常讲的是技术与设备优势,然而在那个肩挑手提的年代,由当地老百姓组成的劳动大军,自发带上家里的铁镢、铁锹、钢钎以及小推车等等浩浩荡荡奔向工地,并用这些简单、原始的劳动工具,挖泥土、凿石头、搬运土石方什么的。不难想象,与其说他们是在修建一道亘古未有的水利工程,倒不如说是把他们的梦想种在贫瘠的土地上,期望长出旺盛的绿意。比如那个叫鹰嘴的高崖,高约三十丈,终日云雾缭绕,哪怕望一眼,也让你头晕目眩。然而,为打通这条生命的血脉,他们中有人徒手像壁虎一样地爬上去,把绳子系在高处的大树上,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在高空作业,把钢钎、锄头的力量,传给大地,传给天边浮动的白云。我相信,他们是在跟天宇、大地以及悠长的岁月对话。我好奇地问,那些修渠民工住哪?哪里有什么床铺,自行解决吃住,反正一到夜里,山崖下、石缝中到处是人,有的垒石庵,有的挖窑洞,有的露天打铺,睡在光溜溜的石板上……霎时,我的脑海里出现呜呜的北风,漫天而降的霜花,还有寂冷的月光以及寒风中夹杂着的几声狼嗥,而这样漫长的夜里,仍能听到一颗颗心在胸膛里火热地跳动。
时间成了唯一的通道,一头连着过去,一头通往现在。在宽敞的纪念馆里,透过一张张照片,你不单能感受到悠然而来又悠然而去的旧时光,还能触摸到那种不畏万难的精神在贲张。随着老师的叙述,我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原树泉。从图片上看年近五十,额上一刀刀的皱纹刻下了岁月的风霜,草帽下的嘴唇边掩饰不住那种质朴的笑。这种笑,来自民间,像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又像是那个时代的写真。那时工程大,石灰用量不小,往往,石灰供应不上叫人发愁。也就是这个时候,原树泉来了,他是自告奋勇来的,他清楚自己烧了一辈子石灰,对个中的比例、用水的多少、特性和色泽的优劣等等了如指掌。于是,许多个日子,他的动作、形貌、笑容成为建设大军不可或缺的动点。另外,还有个叫李百川的老人也不可忽视,他对研制水泥很有一手。那时节,石灰是解决了,水泥却成了问题。你想想,那么大的工程,没有水泥,咋行?人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在这节骨眼上,指挥部多方打听后才知当地有个叫李百川的老人曾在太原水泥厂当过工程师,只是退休在家。于是乎仿效刘备“三顾茅庐”徒步90多里登门求助。此时,正是大雪盈门,也许那一刻老人不为别的,就为那一汪千呼万唤的水,毅然出山了,身后只有雪花静静飘落。
四
汽车转过一个山头,远方一条大红的丝带分外夺目耀眼,它就那么缠绕在几座山之间,宛如火热的存在。直到走近了,才知道这是登上红旗渠的栈道。穿过红飘带,眼前的步道蜿蜒而至半山,红旗渠便静卧在太行山腰。渠水清澈,流速均匀,渠的一侧靠近山体,既是悬崖峭壁,人工錾凿后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一条条的深壑纵横交错,平整规则地一路铺排而去,偶有几棵不知名的树在绝壁上顽强生长着,将它的枝枝叶叶伸得老长。而渠的另一侧呢,就是高磡了,往下一望,是万丈深渊。几只喜鹊唧唧喳喳叫得欢快,像是歌唱那段不朽的历史。我顺着渠道走了约摸一个小时,过创业洞、团结洞后,由郭沫若先生手书的“青年洞”三个镶嵌在岩壁的大字便跃入眼帘,与左侧江泽民主席题写的“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旗渠精神”相得益彰,成为一道难得的景观。
在这里,在今天,我被无言的时光包裹着,被一个个鲜活的却又成为时间深处的面影感动着,他们用双手,用对山川大地和水的无限痴恋,用一个接一个的日子,化不可能为可能,修筑起堪称人类奇迹的“红旗渠”。红旗渠,红旗渠,我反复咀嚼着这个词,仿佛看见一面面红旗在太行山上,在人们的记忆里尽情飘展,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复制的精神坐标。


方欣来,女,湖南岳阳公路人,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青年文学》《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啄木鸟》《湖南文学》等各类报纸杂志,部分作品被选入中学语文试题。著有作品集《夏花微微开》、诗集《时光微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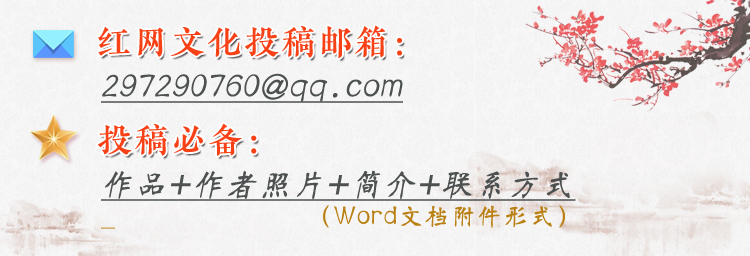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方欣来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化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