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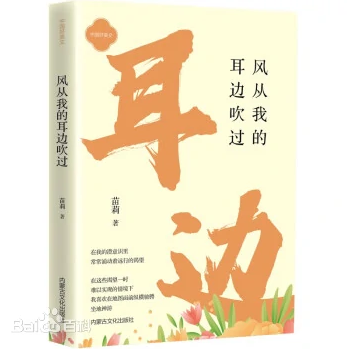
真诚和平常之上的精神发现
文/石绍河
我用两天时间,从头至尾读完河北女作家苗莉散文集《风从我的耳边吹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释卷沉思,觉得她的这些篇什,很好的践行了自己倡导散文“离不开真情实感的支撑”的理念,在环境、人物、细节中贯穿着作家的精神发现和心灵看法,有着从俗世中来,往灵魂里去的奇特效果。
《风从我的耳边吹过》共三辑。第一辑《梅为谁开放》,收入散文二十篇,属思亲怀人之作,其基调是忧伤深情;第二辑《风从我的耳边吹过》,收入散文十三篇,为恋乡寄情之构,其基调是快乐瞩望;第三辑《远行》,收入散文二十四篇,记诗与远方之乐,其基调是宁静陶醉。这些作品尽管题材不一,但有作者独特的面容、观察、思考和书写的方式,是好读耐读的优美散文。
余光中说:“散文家必须目中有人。”苗莉的散文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一个个真实的人。当父亲进入医院时,用无奈的口气说:“反正早晚都有这么一天。”生离死别,万般不舍,都在这句平常的话里。狂风暴雨中,“我”独自行走在泥泞的街道上,恐惧绝望,是父亲撑着一把红油布雨伞,穿着黑色长筒雨靴,喊着“我”的名字走来,“一把拉住了我在风雨中飘摇的手。”(《生命之树》)父亲的形象,温暖的瞬间,刻骨铭心。“年年立春这一天,母亲会早早地准备红布条,逐一扎在每个房门的把手上。”“我感冒发烧,医生来家里给输液,”呼吸困难的母亲一步步挪过来,“守在我的床前,看着药液一滴滴地输完。”(《无雪的寒冬》)姐姐因公伤去世,三百元抚恤金被“外婆用两层手帕包了又包,揣在贴近胸口的衣兜里,一分都没有花过,就那样天天地贴着心暖着,暖着。”(《一树繁花为你芬芳》)深深地大爱就在这些小事、细节上得以体现。黄土高原一个偏远小镇的年轻乡长,见到远道而来的客人,一时尴尬无措,“他搓着双手,一时不知该先为我们张罗什么。”(《在塬上》)一句话就十分到位传神。
在苗莉的笔下,善于刻画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形象,简约明快,印象深刻。“桂花高挑的个子,白皙的皮肤,说起话来快人快语,是个性格爽快的女子。”(《大地无声》)“玉个子不高但声音颇高,皮肤不白但眼睛极美。”(《玉的故事》)“芳芳的外表柔弱,说起话来柔声细语,内心却因为善良的滋润而坚强。”(《生命如花》)武陵源的小挑夫“白白瘦瘦的,很有几分书卷气,”“微笑中透着一个农家子弟的真诚与质朴。”(《秋走武陵源》)还有老增、同桌夏、秀、王三灿等许多小人物,他们平淡真实的出现在作者的生活中,没有柔肠百结的故事,没有曲折动人的经历,更没有豪壮悲愤的呐喊,却让“我”挂念,难以忘怀。苗莉通过自己朴实深情的笔触,描述人性美好的底色,表达深沉内敛的感情,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读到了辛酸悲凉、率真自然、朴实无华和人间温暖。铁凝说过:“被人惦念和惦念别人是幸福的。”“在生命的长河里,若没了惦念,还会有散文么?”读过苗莉的散文,她笔下的这些人物会被读者惦念着。
谢有顺说:“散文最大的敌人是虚伪和作态。”苗莉散文创作一直在真情实感上孜孜以求,突出特点就是写真情,道实情,情味浓,不凌空蹈虚,不虚头巴脑。“红红的火苗欢快地舔着那口大铁锅,升腾着热气,煮熟了一锅金黄的小米粥,蒸就了一排白胖的馒头,使我得以汲取生命的营养,默默品味着一缕缕家的幸福。”(《风从我的耳边吹过》)这完全是由眼前事物触发的内心情感,自然而然,不得不发,毫无做作。“母亲第一眼看见我们姐妹俩时,先是一个愣神,紧接着伸开双臂,左一个右一个把我们俩搂在她的怀里。母亲的怀抱好温暖,母亲的气息好迷人,那是我永远都难以忘记的场景。”(《亲情的盛宴》)母女之间的真情用几个连续动作,画面般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歌如诉。在从神农架返回的车上,一个中途上车的山里汉子把“我”吃了一半的面包、榨菜压在屁股底下,“我不由分说一把将那半包榨菜抛向车外。”“那汉子满含愧疚地站着,如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一样不知所措,那份惶惶然,倒使我一下子不自在起来,忽然为自己的狭隘而惭愧。”(《别了,神农架》)山里人的朴实,作者的愧疚自责,寥寥数笔,纤毫毕现。“蔬菜是人间最平常之物,没有花的娇艳,不比芭蕉、梧桐的诗意,却让我格外喜欢,我喜欢它们生长在泥土里的样子。”(《最美的遇见》)对蔬菜的这份情意来自深切的生命体验,柔软温馨,不含丁点杂质。“我看见一位老人正坐在桌子前准备午餐,洗净切好的菜已经被逐一放在竹筐里,碧绿的空心菜、饱满的芸豆角,还有一盘红红的辣椒。虽然已经迟暮之年,老人却依然精心打理着生活的细节。”(《诗情画意美合川》)作者满含爱意地赞美普通人的生活态度,蕴含着深深地人民之情。告别武陵源的小挑夫时,“不知他从哪里买了几个黄澄澄的橘子送我,我不忍收下又难却他的好意,就拿了两个。”(《秋走武陵源》)在大宁河,“抱过来小姑娘单薄的身子,紧紧地,犹如抱着自己的孩子。是大宁河的青山绿水赋予小姑娘善良的品性,也赋予她一颗纯真的爱心。”(《期待无限》)人性之美跃然纸上。
散文是灵魂的叙事、人心的呢喃。苗莉的作品没有宏大叙事,写的大多是日常琐事,身边人物,基础材料来源于其生活世界,因而根扎得深,有一份从容和自在。她写日常生活、世俗人情,用优美的人情写人性、人生、人心,写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把意境美和人性美融合在一起。
梁实秋说:“有一个人便有一种散文。”苗莉“常常涌动着远行的渴望”,工作之余经常南下北上,东出西游,“远方的美丽与陌生,每次都能带给我诸多新鲜的感受,就像生命中滑过的片片流云、缕缕清风。”(《远行》)她因此写下了大量优美的散文。当同行者阿慧把一朵盛开的蒲公英递给我,“觉得这朵蒲公英,仿佛就代表着真情和善意、亲情和仁爱。”“站在长满芦苇的河边,看日出映朝霞,那是我心中最初的诗和远方。”(《遇见淮阴》)在武隆旅行,她喜欢“仰望天空繁星闪烁”,留意打糍粑,观看祝寿仪式,和年轻媳妇聊天,甚至注意到一只大南瓜、鲜亮的辣椒,心地是纯净和安宁的(《远方的武隆》)。在白马山的一座农家小院里,“我”对红红的柴火感兴趣,坐在火边吃煮熟的玉米,享受回归自然的轻松。女主人做的豆花,香味原始而纯粹,在这里,“我们离人间的烟火很近,离心灵的宁静很近。” (《最美的遇见》)她称这是“最美的遇见。”到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旅游,她不去写奇峰三千、秀水八百的美景,却浓墨重彩写一个小挑夫,风景里的人物比风景更有质感,赋予无限美的内涵。太行山深处的英谈,黄巢起义军曾在此屯兵,建立营盘。还留有八路军总部办公室,刘伯承、邓小平故居。面对这么厚重的文化积淀,苗莉没有钻故纸堆,追寻发掘人文典故,没有大段大段缅怀历史,而是点到为止。她观照历史,更注重现实和当下,把历史与现实、写实和抒情巧妙结合起来。她写在英谈遇见的忙农活老人恬静安详的眼神,从古井里坚定而熟练地汲水的姑娘,玛瑙色、艺术品一样的玉米棒,细碎的阳光、摇曳的光斑等(《釉色英谈》),从一些小事来反映大的主题,表达自己的文化关怀。
苗莉的这些旅游散文并不以描写山川胜景见长,而是另辟蹊径,写自己的见闻观感,写风景里的风俗、人情、花草,用简单写复杂,以平静写热烈,抒写她在风中飞翔,尽情享受的心旷神怡,表达在大自然怀抱里自由自在放牧心灵的缱绻情怀,体现极高的艺术造诣。


石绍河,苗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家界市作协主席。现供职于张家界市自资源和规划局。出版有散文集《清泉石上流》《大地语文》,主编多种文选。
来源:红网
作者:石绍河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化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