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梦
文/汪小说
一
穿过一条条曲折的街巷,他找到巷子最深处那家古董店,走了进去。柜台后戴眼镜的老人缓缓抬头:“请随意看看。”
他瞠目立于原地:“这家古董店是您开的吗?”
老人摘下眼镜看他,从柜台后走出来:“是我开的,怎么了年轻人,要采访我吗?”
“不,没什么,我只是随口问的。”他低头看了看脖子上挂的相机,这身打扮确实像是一个记者。
老人笑了笑:“别紧张,随便看看,只要不损坏,拿在手里把玩也没关系。”
“铛——”店里的落地钟敲了两下,他循声望去,下午二时,屋子里除了他和店长,没有第三个人。店里亮着昏黄的水晶吊灯,阳光透过玻璃彩窗在素纱窗帘上投射下梦幻的阴影,窗边一个烟斗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拿起烟斗,突然呼吸一滞,烟嘴上分明刻着那个名字。
“以后我要开家古董店,门口的告示上写‘洋人与狗禁止入内!’”他想起烟斗的主人在护送文物逃亡时曾得意地笑着对他说。所以他找了百年,百年间他辗转于各地古玩市场,推开一扇又一扇古董店的大门,却始终不曾看见那人的身影,直到今天。他几乎要抑制不住地淌下泪来,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他转过身去问店主:“这支烟斗您从何处所得?”
老人接过烟斗,戴上眼镜端详。“大概是二十年前,我在上海的古玩市场偶然淘得,我想想。”他把烟斗伸到阳光下,“对,一个叫楚奕的人,这儿有好多东西都是他的。”
“你见过他?”他怀着一丝希望试探地问道。
“不,当然没有,是他的孙辈在体育场售卖的。他们说这是传了好几代的古董,但是他们这一代家业衰败,只好把这些古董卖了来维持生计。”老人说着怅然地摇摇头,“保护了这么久的东西被后代收走一纸支票就交了出去,实在太可悲了。我怕这些古董落入不识货的人手里被糟蹋了,于是全部买了下来,每日细心地擦拭着,也算是告慰物主吧。”
“谢谢您。”他想那个人要是知道自己无比珍视的宝贝被后辈转手卖掉,定要气得拿烟斗挨个敲他们的头了。
“不必谢我,我也不过是暂时保管。”
他看着一件件被陈列在展示架上的古董,耳畔响起离别前那个人说的话:“我奉旨将文物运往南方,便势要与它们共存亡。只是我家中老小还有木匣里的东西,请你帮我平安护送到上海,那里会有人接应你。不知是否还有重聚之日,请一定保重,待时局安定,我们再相见。”
沉重的回忆压得他喘不过气,他不愿在此久留便托词离开。
“好,我送你。”老人替他拉开门,刺眼的白光使他感到眩晕,他刚踏出门槛便跌进时空的陷阱。
二
从乱尸堆中爬起来,孩子张大了嘴巴呼吸,方才母亲把他紧紧抱在怀中,他安分地酣睡着,直到温暖的怀抱逐渐变得冰冷,他才挣出母亲僵硬的臂弯。身下黏腻的血水将道路染得猩红,好似上元节那天母亲牵着他去放花灯时走过的街道。可是眼下街市里的人纷纷倒地,他们脸上不再有笑容。他惊恐地推推母亲,正欲问这是怎么回事,却见母亲的背上扎满了箭矢。孩子怔怔地看着,呼唤母亲几次却发现再无回应,大哭起来。
“报——将军,前面有残党。”
“什么残党,不过是个小孩子,带过来。”
男人抬抬下巴,手下的士兵便把孩子抱了过来。他单手提起孩子置于身前:“不许哭!”
小孩被他的呵斥吓了一跳,战战兢兢地抬眼看他,飞溅的鲜血凝固在男人的脸上,使他如同民间传说里的食人魔一样面目可憎,孩子呜咽几声便又哭号起来。
“将军,这四周有野狼出没,把他丢在这儿,他也活不长的。”
“谁说我要杀他?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把他带回军队养几年充当兵力,多一个人总是好的,你们懂不懂?”
“是是是。”士兵们听了他的话纷纷点头,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是他的私心。
他缓缓驾着马,面前的孩子已经哭累了,趴在马背上睡着了。
行至军营,他把还在梦中的孩子拎入帐内摇醒。
“你叫什么名字?”
孩子迷迷糊糊地揉揉眼睛,一睁眼看见陌生又可怖的面孔,哭喊着:“不要吃我,不要吃我!娘亲救我!”
男人疑惑地皱眉:“我不吃人。”他低头看见酒杯里自己的倒影才反应过来,不禁哑然失笑,无奈地用湿布擦净了脸,才转头对孩子说:“好了好了,这回总行了。”孩子看他一眼仍止不住地哭,他被吵得头痛,于是捏住孩子的脸:“听好了,你娘亲死了,你若不想死,便给我安静些。”
“死?”孩子噙着泪抬眼害怕又疑惑地看他。
他看着这双明亮的眼睛心中惶恐,便匆忙避开视线:“就是再也不会给你做饭吃了,再也不会同你说话了。”
孩子的肚子发出“咕噜噜”的声音。
他叹了口气,掏出怀里冻得僵硬的饼递给孩子,黑瘦的小手一把接过。
“名字。”
“没有名字。”
“怎会没有?”
“没有父亲,没有名字。”
他沉默地看着狼吞虎咽的孩子,心里不是滋味。
“跟着娘亲,没有饭吃,跟着你,有大饼吃。”
真是有奶便是娘,他觉得可怜又可笑,泪水和鼻涕还分明挂在脸上,现在却抬头冲他没心没肺地笑。
“延生。你的名字是延生。”延生,延续生命,代替亲人们好好活下去吧。男人摸摸孩子沾满泥土与血渍的头发说。
“那你呢?”
“楚奕。”
“楚奕!”
“要叫我将军!”
“楚奕!”
“当心我把你丢掉。”楚奕阴沉着脸,恶狠狠地揪住孩子的衣领,作势要把他提出帐外,延生愣愣地看着他,而后眼泪便夺眶而出。楚奕瞬间慌了神,急忙松开手,“骗你的,我不会丢掉你的。”他看见延生就想起被他杀死的懦弱的自己。
楚奕第一次真正萌生出把这孩子丢掉的想法是在带他到操练场时。延生随他站上高台,看着底下的士兵整齐地挥动长矛,精准地射出箭矢,突然想到了可怜的母亲的死状,便不住地颤抖起来,接着号啕大哭。不论如何呵斥或是安慰都止不住,楚奕只好让小将把他抱到军帐中去。
第二天楚奕发现延生不见了,小将如实坦白,是他把延生带到了山上,楚奕没说话,算是默许了。
无用的棋子便该剔除,这是他的“父亲”曾教他的行事之道。
日落时分,楚奕正担心夜晚山上会不会有狼出没,没想到延生携数枝桃花奔到了他面前。
“楚奕你看!”孩子满脸欢喜,像是在等待着他的夸奖。
“真好看。”他心虚地拍了拍延生的头。
“送给你!”
他接过桃枝。花瓣上打着落日的柔光,像孩子冻得红扑扑的小脸。
既然拿不了武器,那便教教他行兵策略吧。他暗自思忖。
“楚奕,春天是不是到了啊?”
是啊,春天到了呢,他似乎听到有冰雪融化的声音。
延生学东西很快。
延生很机灵,鬼点子也多。
延生很受大家宠爱。
延生……
延生确实是个好孩子,但如果有一天发现自己是被仇人养大,会不会恨他呢?望着已经能够自己翻身上马的延生,楚奕开始害怕那一天的到来。
他把延生叫到身边来,看着这个快赶上他高的少年,觉得恍惚,捡到延生时分明还是个才到他膝盖的猫儿一般瘦小的孩子。延生睡觉时总爱把身体蜷成一团,维持着当年在母亲怀里安睡的姿势,夜里常常在梦中啜泣,楚奕看着心疼,把他揽进怀里,轻轻拍抚着孩子单薄的脊背,十岁那年的夜里,他也曾希望有人能这么对他。可现在他再也不能将延生单手抱在怀里,让他骑在自己的肩头,带他去看春日里的原野。
“什么事啊?这么盯着人怪恶心的。”延生嫌弃地后退半步。
楚奕苦闷地发笑,伸手去捏他的脸:“你何时变得这么别扭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没这样啊。”
“偶又不素你的孩组(我又不是你的孩子)。”因为被他扯住脸颊,延生说话含糊不清,挣扎着拍开他的手。
楚奕松开手,背过身去没再言语,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延生真相,只对延生说过他是捡来的。延生也不多问,听话地跟在他身边,用功读书,在军中待了十余年。楚奕看着延生就像看着他自己,可他又怕延生成为第二个他。他是亡国之奴,生时命不归己,死后亦无墓可葬,他不希望延生也这样,这个孩子应该看他未曾看过的世界,替死去的他再活一次。
延生二十岁生日这天,楚奕的军队正因抗击晋国有功受到封赏,将士们聚在一起庆祝。其实延生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已经无从知晓,他们默认是楚奕捡到他的那一天。大家把延生和楚奕推上前去讲话,延生支支吾吾半天讲不出一句话,楚奕端起酒杯说:“早日结束战争,还天下太平!”随即仰头一饮而尽。众人叫好,也端起酒盏。
宴会散后,延生和楚奕围在火炉旁取暖。“今年的冬天好像格外漫长。”楚奕将温好的酒递给延生。
延生双手捧着酒杯没有喝,他扭捏了半天,开口说:“其实我刚才是有话要讲的。”
楚奕咂舌:“我去把他们叫回来听你说。”
延生忙拽住他的衣袖:“别去。”楚奕忍不住笑出声来,延生才知道自己被戏弄了,于是赌气道:“你又笑我,我不说了!”
楚奕强忍着笑意坐到他身旁:“好了好了,我不笑了。你说吧。”他摇摇延生的手臂:“延生,说说嘛。”
延生拗不过他,推开他的手说:“我想说,谢谢大家,让我在这儿的十六年里每一天都过得很高兴,还有……”他低下头深吸一口气,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而后抬起头看着楚奕说:“谢谢你,楚奕。”
他的眼中有火苗跳动,他呈上一颗烈火淬炼的真心,可是楚奕不敢接过,偏过头不去看延生,唯恐将自己最阴暗的一面暴露在火光之中。
半晌的沉默之后,延生终于扯扯他的衣摆:“你也说点什么啊。”楚奕回过头,看见延生红得要滴血的耳朵。
“延生,你有什么愿望吗?我一定会帮你实现。”
“不知道,我没有想过……那你呢?你的愿望是什么?”
楚奕轻笑一声:“我刚才说过了啊,希望现世安稳,天下太平。”
“我的愿望就是实现你的愿望。”
楚奕看着面前的人说不出话来,延生的眼睛就像晴朗的夜晚,里面有繁星与灯火,他从这双眼睛里看见了自己——面目可憎的怪物、吃人嗜血的恶魔。他把手伸向燃烧的火炉,说道:“好啊,只不过我可能等不到愿望实现的那一天了,但是延生你可以,你会替我看到太平盛世。”
楚奕听闻秦军将要南下进攻的消息,心中明白战火早晚会烧到他这里。他的军队在与晋军交战的时日里早已元气大伤,兵力不抵秦军的十分之一,到那个时候,他还能带着众将士披荆斩棘守住城池吗?他没有信心。
“我会为你献出良计击退敌人,尽早结束这乱世,你不相信我吗?”
“我当然相信你了,延生。”楚奕伸手要抚摸他的头,惊觉对方早已不是小孩子了,又收回了手,“好,我们都会看见。”
果然,战火在第五年烧到了河对岸,前面的城池一座接一座地陷落,楚奕知道他不能再逃了。
作战前一晚,楚奕走进延生的营帐。延生从成堆的竹简中伸出头问他:“什么事?”
楚奕坐在他身旁,像是第一次见面似的,仔细打量着他。
延生被看得不自在了,摸了摸后颈说:“我明天还是和你一同上阵吧。”
“你又忘记上次的教训了,你的腿伤还没好,如何能行动?”
延生的腿伤是旧疾了,在被敌军用毒箭射中右腿后他好不容易才捡回一条命,在那之后楚奕便不再让他随自己一同上阵了。冬月里延生眼见敌军临近,整日操劳,在下练兵台时由于体力不支竟摔了下来,腿伤便又复发了。
“哦。”延生悻悻地低下头。
又是许久的沉默后,楚奕终于开口说:“延生,你和我很像,我在十岁的时候被敌国的将领选中,他训练我,让我成为他的‘兵器’,对我来说,他是‘父亲’,也是仇人,他让我从万人践踏的战败国俘虏变成统管千军的将军。你说,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呢?”延生没有说话,楚奕其实也并不期待他的答案,自顾自地继续说:“所以当我看到你时,我就想起那时的我自己。我想救你,可我又有什么资格呢?你的母亲是被我杀死的,延生,你恨我吧。”说完他闭上了眼睛,不敢看延生。
“不是你。”楚奕讶异地转过头,“是楚国,是楚王,但不是你。你是想救天下人的,不是吗?”
“可我并不能。我杀了太多人,我没有救下任何人。”楚奕声音喑哑。
“你救了我。”
“敌方实力强劲,此战切不可掉以轻心。”
“延生,这句话你说过五遍了。”楚奕说。
延生没有理他,继续说:“必要时打开我给你的锦囊。”
“知道了,知道了。”楚奕骑上战马,拉住缰绳。
“还有,”延生叫住他,“平安回来。”
“嗯!”他不知道能否活着回来,此程一去只怕是凶多吉少。他们都知道。
前方传来胜利的消息,延生被人搀扶着走出帐外,这些时日他常不能安寝,一闭眼就想到母亲死去的情形,接着是楚奕,于是被吓出一身冷汗,腿伤也愈发恶化。
延生站在帐前迎接归来的将士,但却迟迟不见楚奕的身影。直到后面的人抬着一卷军旗走来,不祥之感笼罩全身。延生颤抖着掀开残破的旗帜,看到一张熟悉的脸,还未干透的血迹凝聚在嘴角。
“他怎么了?”延生明知故问。
“楚奕将军,战死了。”
视线逐渐模糊,却见地上的人手里似乎握着什么,延生想打开他的手,那只手竟死死地攥着,延生将握紧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从手心里掉落出一枚香囊。延生打开香囊,里头装着的,是桃花花瓣,片片花瓣被鲜血浸染。这是出征前延生为他做的平安符。
楚奕终究还是看不到“现世安稳”的局面了,他说要延生替亲人们活着,要替他活着,代他看现世安稳。但他能看到吗?他能等到这一天吗?二十五岁这一年对延生而言是一场新生,他为此永远活着。
三
延生第二次遇到那人已是千年之后了。他替那人看了太平盛世,他经历了无数次朝代的更迭,内心已毫无波澜,于是他隐居山林,与世隔绝。直到那天,少年的闯入打破了他平静如死水般的生活。
芦花鸡落在延生面前的时候,他以为天上真的会掉馅饼,而后才发现鸡翼上插着的箭。许是山下的村民射中的吧,这样想着,他便坐在门口等待失主上山来寻。
不一会儿,便有一少年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延生懒懒地看了他一眼,却突然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楚 …… 奕?”延生的声音颤抖,满脸不可思议的神情,他没想到能再遇见楚奕。
少年有些吃惊地看着他:“你为何知道我的名字?”
延生跑过去紧紧抱住他:“真的是你!太好了,太好了……”
少年在他怀里挣扎:“放开我!我不认识你!救命啊!”
延生这才意识到这一切太过奇怪,他松开少年,仔细瞧着。这张脸虽有些稚嫩,可像极了楚奕年轻时的模样,他不死心,又问道:“你真的不认识我?我是延生啊。楚奕,别再捉弄我了,我等了这么久才终于见到你……”他说着便落下泪来。
少年看着面前比他高半个头的怪人突然抽噎起来,顿时手足无措地安慰他说:“你先别哭啊。你说的楚奕确实不是我,不过我下山后可以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村里有没有同名同姓的人。那个人跟我长得很像吗?我回去再问问我爹,我是不是有个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兄弟,爹一定会臭骂我一顿……”
延生被他逗笑了,擦干眼泪说:“对不起,我太激动了。”他想着自己活了这么久,却在一个少年面前掉眼泪,还被他安慰,实在是太丢脸了。“你不必去帮我找那个人,他已经不在这世上了。”他转身提起掉在门前的那只芦花鸡,“拿着。”他伸手把鸡递给少年。
延生问他:“你是谁家的孩子?”
“山下猎户楚元家的,我爹的射猎水平可是村里第一呢。”少年骄傲地说。
看来他真的不是楚奕,延生心想。“那好,你明天还会到山上来吗?”他期待地看着少年。
“不知道。”少年移开目光,“我得走了,不然爹该担心了。”
延生看着他跑下山去,逐渐消失在树林中。第二天一早延生便坐在门口等待少年的到来,可太阳都快落山了也没有见着一个人影。就在他怀疑昨天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他的幻觉时,一只鹌鹑从天而降。
少年急匆匆地跑来,脸颊上挂着细密的汗珠,他喘着气对延生说:“我的鹌鹑掉你这儿了。”
延生笑着将那只鹌鹑递给他。
少年摇摇头,说:“送给你的。”
“为什么?”
“我爹说,若要跟人交朋友,就送他一只自己打到的猎物。”
延生笑而不语,把鹌鹑提进厨房。少年站在屋外,看延生在屋里忙碌。
“你在做什么?好香啊。”少年忍不住开口问道。
延生端着一盅汤从屋内出来,放在外面的石桌上,才招呼少年道:“好了,过来吃吧。”
“鹌鹑汤?”
“嗯,尝尝。小心烫。”
“好喝!你是怎么做的?我从不知道天底下还有这么美味的东西!”少年抱起汤盅就喝,随后被烫得像小狗一样伸出舌头来呼着气。
“当心点!”延生笑得合不拢嘴,“你说得也太夸张了吧。”
“是真的!我爹做饭可难吃了,但我又不能说,只好硬着头皮吃完。当然我自己做的也不怎么样……”
“那你娘呢?”
“娘在生我的时候就死了。”
“抱歉。”
少年摇摇头,好像这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值得悲伤的事,延生却觉得心疼。少年抱着汤盅喝完最后一口,转头问延生:“还有吗?”
延生笑笑,拍了拍少年的头:“没了,想吃明天再来吧。”
“对了,我还没问你的名字呢。”
“我叫延生。”
“你是哪儿的人?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我一直住在山上,不曾出去。”
“一直?”
“嗯,大概有一千年了吧。”延生冲他邪魅一笑。少年打了个寒战,延生大笑起来:“骗你的,我又不是鬼怪。只是我确实一直住在山里,没有人见过我。”他说了谎,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又存在了多久,他只记得他给许多人当过军师,他们或称王称霸,或曝尸荒野。可不论他站在哪边,放眼望去,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后来,他便躲进了山里。
少年松了口气。“糟了,我得回去劈柴煮饭了!”他跑了几步又折回来对延生说,“我明天会再来的。”延生笑着点点头跟他说再见。
往后的日子里,少年总会提着野味到山上来,而延生也会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少年同他讲山下发生的趣事,延生则教他功课。
转眼已过了五年,这天少年又上山来,他对延生说:“朝廷征兵,我得跟随同伴们去打仗了。”
延生这才发觉自己已经需要抬头看他了,他飞扬的神色和当年的楚奕如出一辙。
延生说:“我和你一起去。”
少年惊讶地看着他:“可你不是不能出山吗?”
“谁说不能的?只是我不愿意。”
“那你现在为何愿意了?”
延生被他问住了,反问道:“那你呢?你是自愿去打仗的吗?”
“当然,外族入侵,我怎能坐视不管?你不是教过我,‘大丈夫生于乱世,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况且今天若我不上战场,明日那些人就会来杀村子里的人。”
延生说:“我和你想的一样。走吧。”
他又做回了军师。
延生无数次目睹在这名为“天下”的棋盘上,黑白双方相互厮杀,而时代造就的这场棋局中注定有一方要败下阵来。一局终了,白子覆灭,又会有新的白子重回棋盘。他曾是执棋者,也是观棋人,博弈的戏码他看得够多了。然而无论哪一方胜利,棋盘之外还有那么多棋子,他们不曾入局却又从未脱离棋局,被动地接受着局势所带来的突变,无人过问他们能否承受这一切。没有哪个王朝能实现他的愿望,实现局外棋子的愿望,他明白,弱肉强食的时代里战争不可避免,人们把人间炼狱称作世界。
时隔千年他重回棋局,这一次他不为任何一方,只为保护手中唯一的那枚棋子。他以为他可以,然而纵使他有再大的本领,也无法挽救早已日薄西山的王朝,就像许多年前他不能救下楚奕一样。黑子很快吃净了白子,而他手中的那枚棋子也未能幸免。
延生把楚奕带回了故乡。他们离开的时候正值冬天,他记得他踮起脚帮楚奕拂去头上的落雪,那时楚奕对他说他们一定能凯旋,到时候就带他去看山下的村子,狩猎大会时捕获最漂亮的孔雀送给他……延生再回去时,芳香遍野,春回万物生,所念之人就葬在他屋前的桃花树下。
延生不愿再回忆过去,他受够了上天的愚弄,于是逃离了家园。当永生者徘徊在无尽的白天与黑夜间,命运的骰子,已向世界亮出了它的点数。从始至终,他都未曾逃脱命运为他设定的棋局,他早已无法置身事外,一切皆不可回头。
他想他是被命运诅咒的人,而给他下咒之人正是楚奕,又或许是在二十岁的夜空下许下诺言,便注定了他一生都要与楚奕相遇——他在安禄山叛乱时,遇见的是仗剑奔走、投往郭子仪麾下的楚奕;在元军步步紧逼时,遇见的是长歌当哭、以死殉国的楚奕;在列强入侵、国家内忧外患之际,遇见的是奉朝廷之命将文物护送到南方,最终生死未卜的楚奕。那也是他最后一次遇见楚奕,但他确信,他们一定还会再相遇。
四
“忘了问,您贵姓?我还真想为您写一篇人物专访。”他站在门口,回过头来问,双手不自觉地握紧。
老人望着他羞红的脸颊只是笑,而后如狐狸般狡黠地眨眨眼睛:“楚奕。”
他瞪大了双眼,呼吸急促起来。两个人的容颜逐渐变得年轻鲜活,白发变青丝,变成他们第一次遇见时的样子。延生正要伸手抓住这个从他身边逃离了无数次的“叛徒”,对方却将门紧紧关上,隔着厚重的玻璃,说:“回去吧,延生。你该去看看崭新的世界了。”
“不要,我不要!你又要丢下我吗?”
他骂楚奕混蛋,他感觉自己的肉体和灵魂都像被对方操控着。楚奕要他永生,要他看太平盛世,现在又要将他赶回去,要他新生,仿佛过去种种皆是如梦幻影。这不公平!
可他还是照做了,他走出院子。
落地钟敲到第三下,穿长袍的男人与古董店一起消失在白茫茫的一片日光里。
(原载于2023年第5期《创作》)

汪小说,原名汪立说,生于湖北襄阳,长于广东深圳,现就读于广州大学。作品散见于《西部》《参花》《椰城》《连云港文学》《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等报刊及选本,部分作品曾获各级奖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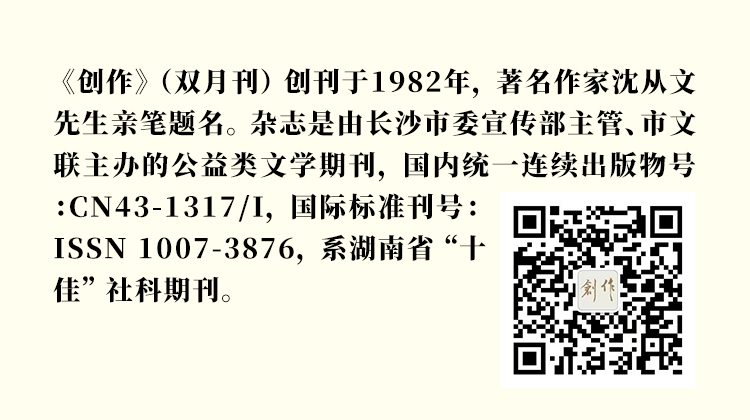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汪小说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化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