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史诗的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
——读《黄河长调》给李立的信
李立兄你好!
对于兄这样一部厚重、广博、体量极大、气象恢宏的诗作,把握起来确实有一定难度和挑战,也正因如此,反复品读才更见滋味。在读大著的过程中,我每每停下来沉思,如果让我来评价这些丰饶的诗行,我该说些什么,才能对得起诗人这份倾注心血、遍历山河的真诚书写?要说、想说的话其实很多,一时却难于找到恰切的入口。这就如同面对一个巨大而完整的球体时,人们总难免一时失语,所谓“震撼”云云,不免有夸大言辞或表达无力之嫌,而如“岱宗夫如何”那般,一时说不出究竟“如何”,反倒更贴近那种初遇大美时的真实状态。后来,我读了吕本怀和陈啊妮两位诗歌研究者对兄这部大作的评价文章,心里就释然、踏实多了。因为他们二位精准而深切地说出了许多我想说的话,尤其是吕本怀的文章,条分缕析、见识明通,完全可以当作大著的导读来细读。我不是职业的诗歌批评家,只是一个在诗歌中摸爬滚打多年、至今仍热爱写作的业余诗歌爱好者,不可能对大作做出吕、陈二位那样系统而高屋建瓴的评说,我只想从一个诗歌操作者和普通读者的双重视角,谈一些我不太成熟却发自内心的想法,供兄参考和一笑。
首先,我觉得兄的大作,有“创体”之功,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和探讨。
曾有一度,诗界尤其是一些具有远见的诗歌评论家不断呼唤过新的“史诗”的出现,著名诗歌评论家、我的大学老师杨匡汉先生就是其中发声较多、也较有力者之一。然而,就我的视野所见,这些年来能够真正称得起“史诗”气象和格局的作品其实并不多见。杨健的《哭庙》、大解的《悲歌》可以说是有创新精神和探索意识的作品,但他们的本意还是在挖掘和反思中华民族的根性与传统,我个人以为,从文学脉络上看,仍可视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滥觞与延伸。更早一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杨炼的《诺日朗》和江河的《太阳和它的反光》也明显是在文化寻根,而且是以短制、组诗的形式呈现,气魄虽在,但规模和体量上还不好称得起“史诗”这个名号。
从根本上说,对于什么是“史诗”、史诗在现代性语境中该如何确立,诗界至今并没有一个趋于一致的共识。一来,我国的汉语史诗传统确实不太丰厚,能被广泛认可的也就《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等几部少数民族的史诗,即便如杜甫的《北征》、“三吏三别”等,学界一般也不好直接算作“史诗”,更多是看作“诗史”;二来,作为中国现代诗重要传统资源之一的外国诗歌,其从《伊利亚特》《奥德赛》开始并延续的史诗传统,虽然早有译介,但在汉语中新诗创作中,并没有多少真正移植成功的显著成果。在现代诗歌中,孙毓棠的《宝马》是很好的一部历史叙事长诗,气韵沉雄,但也不好直接以“史诗”谓之。至于如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等一大批长篇诗作,尽管当时影响不小,但现在看来,也大多只能归于长篇叙事诗的行列。还有一点是我的私下猜想,就是,即便有些诗人内心怀有创作史诗的宏图大愿,但对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史诗这类宏大创制,多少是存有犹疑的,怕费尽心力却吃力不讨好。可能确实有一些诗人也在默默尝试,但作品出世的几率比较小,即便出世,受限于传播环境,也很难被广泛阅读和讨论。在这个背景和现实下,兄这部大作的面世,确实令我耳目一新,心中为之一振。吕本怀的文章称兄的大作为“当代边塞诗的扛鼎之作”,在一定意义上,这一判断是成立的、说得也没错。不过,我倒以为,不妨更开阔地命之为“当代史诗的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自然,《黄河长调》中有不少篇章可以列入边塞诗的行列。然而,边塞诗毕竟是一个历史积淀深厚、风格指向比较清晰的命名,拿它来定义《黄河长调》整部诗集,我觉得帽子似乎小了,格局略窄了,至少,像《上海谣》《东北大平原》《南海蓝》《大地》等气象各异、意蕴深远的篇什,就不好简单列入边塞诗行列。
我说的“创体”之意还不止于此。兄长期以来被诗界称为“当代行吟诗人”,在“行吟”二字上,兄在身体力行层面绝对是佼佼者,走完大陆边境的壮举令人神往钦佩,而把“行吟”付诸笔端、转化为诗行,创新的勇气和实绩更是令人惊叹。你在后记《八千里路云与月》中有详述创作历程与心得,不需我赘言。有宣言,有实绩,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这是最值得肯定的诗人品格。初读大作后,我特意又读了一遍英国诗人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这倒不是拉大旗作虎皮,而是想在对照阅读中找到某种精神气质和写作方法上的契合。茅盾先生曾这样评价拜伦这部长诗:“原作上下古今,论史感怀,描写大自然,包罗万有,洋洋洒洒,屈原《离骚》差可比拟,而无其宏博。在西欧,亦无第二人尝此格。”在我看来,这段精辟的评价移至对《黄河长调》的认知上,也有一部分深刻而准确的相似之处。尤其是“行吟诗”这种“格”,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现当代诗坛还少有人像你这样以整部诗集的大规模、有系统地大胆尝试过。据说,拜伦的那部诗在当时曾经是一部有名的“旅行便览”,他以诗笔生动描写了葡萄牙、西班牙、希腊、阿尔巴尼亚、比利时的滑铁卢及莱茵河两岸、瑞士的莱蒙湖、意大利几乎所有的名胜古迹,融地理、历史、人文于一体。而你这部长诗描写的内容之广袤,也几乎涵盖了祖国所有边疆省区、山川湖海、风土人情。单就这一点,也还有得一比,绝不是攀龙附凤。孔老夫子说过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中那么多的植物、动物、地名、民俗细节,令人目不暇接,打开了阅读之外的另一扇窗户,增长了见闻,也拓宽了诗的疆域。拜伦的吟游是忧郁的、沉思的,带着浪漫主义的愤世与感伤;相比之下,你的行吟是开阔的、昂扬的,充满一个时代行者的豪情与审视,彼此都契合了各自时代的风云与精神。
其二,这部诗集的语言探索和呈现方式,为现代汉语诗歌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和路径。
新诗诞生一百多年来,如何确立新诗的语言形式,如何摆脱文言阴影、又超越口语贫乏,一直众说纷纭、实践各异。黄遵宪提倡“我手写我口”,强调通俗与亲切。胡适有《尝试集》的初步实践,开辟草创之功。闻一多、徐志摩等人探讨新诗格律,追求建筑美与音乐美。近二三十年来,有关“口语诗”和“书面诗”的争论更是从未停止。这些现象说明,新诗诞生以来,诗歌界对相对于古典诗歌的成熟稳定而呈现出的“未完成”和“实验”状态是不甚满意的,是有点“底虚”的。诗歌作为一种高度凝练的语言艺术,其“手艺”也就是语言的操控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形式和内容向来是不可以分离的。“诗到语言为止”,强调本体,不错。诗歌要有“诗家语”,追求独特表达,也没错。诗歌要“陌生化”,打破习惯性阅读,也有道理。我的想法是,地上本可以走出的路有好多好多,大家不妨按自己的路数、自己的心性走走看,也许最终能走出一条被更多人认可和共鸣的语言道路来。新诗百年来的实绩就是很好的证明,多元并存,百花争艳。
说老实话,初读你的大作,作为一个同样在写作中摸索的人,我对你这样的写法是心存疑虑的。语言的直白、节奏的粗粝、大量的散文式陈述,甚至被人视为过时的直接抒情……这,能真正写好吗?我当初确实为你捏着一把汗呢。然而,静下心来,一路读下去,我的疑虑渐渐被打消了,转而成为一种钦佩。“诗,为什么就不能是这个样子呢?谁规定的什么样子的诗才算是诗?”穿衣服要讲究“搭配”,诗亦如是,讲究内容与形式的契合。你笔下那浩瀚的山川大地、多彩的风土人情、厚重的历史沉淀,正需要这种汪洋恣肆、不拘一格的语言来表达,非如此,就会显得纤弱、小气或者矫揉造作。更令我耳目一新的是,在貌似平常、不加雕琢的语言外衣下,不断有结结实实的、闪着智慧光芒的格言警句跳出来,击中人心,就像交响曲《蓝色的多瑙河》中那些不断迸发、金光闪闪的华彩音符。
我随手对下列句子画了红道道,常读常新,例如:“所有的水,都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岩石是打开可可西里话匣子的金钥匙”“千万不要去尝试少女的柔情,一旦陷进去就不能自拔”“许多事物原本就没有谜底,有也贵在知而不言”“任何时候坚强是自己唯一的港湾”“那些雪可以落在我的头上、肩上、脚上/甚至心上,它们不可能为我而融化”“人们的脚步到不了的地方,心到了”“雪山是用来仰视、崇敬,用来信仰的”“平和在海之上、持重在海之上、海拔在海之上”“在一个人的脸上雕琢笑容,需要费尽心机”……这样的句子太多了,遍布全书!这些诗句,正说明了最深刻的真理往往是朴素的这个道理,也说明,真正有力的诗的语言必然是经过生命体验反复咀嚼、最终汇入诗人血液的语言。只醉心于诗内技巧,产出的容易是精致的“技术品”;而打开心胸,接纳八方风雨,做足诗外功夫尔后再返观诗内,才容易诞生浑然的“艺术品”。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翻译者杨熙龄先生在游记导读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游记》的词句单个读来略显俗气,但这份俗气最终会被积少成多的感染力湮灭。”若将“俗气”二字谨慎地换成“粗粝”或其他类似字眼,来描述我阅读《黄河长调》的真切感受,也许是比较贴切的。这强大的感染力就在于,你毫无保留地将自己那颗赤裸的、真诚的心置于天空、大地、历史之间,无遮无拦,而那盘旋上升的诗意回声,必将在无数读者心头久久缠绕,引发回响!
其三,这部诗集为类型化写作如何在保持风格的一致性和避免自我重复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对当下汉语新诗创作诟病最多的,恐怕就是同质化、模式化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诗人思维的矮化和平庸化。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在此按下不说。具体到诗人个体,重复自己、复制经验也许就是停滞不前甚至退步的开始。再具体到像这部长诗一样的鸿篇长歌,我称之为一种特殊的类型化写作,最容易出现重复,包括意象的重复、套路的重复、语义的重复、起承转合的重复等等。令人欣喜的是,你这部长诗,较好地避免了类似的缺陷。我以为,你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从中可以清晰体会到你的匠心和经营的苦心。
在保持总体风格一致、气韵贯通的前提下,你在每一单独篇什的谋篇布局上都下了实实在在的功夫。首先是寻找独特而精准的切入点,给每一个篇什都提炼出一个突出的而且是有说服力的“诗眼”,找到一个如何进入的路径,如何展开、铺排的流向,以及如何收束的休止符,让每一首都有其独立的生命。举几个我在阅读过程中触动最深、笔记最多的例子。《青藏高原》,因为每每有人去朝拜、书写,人们心目中就容易形成固化的神圣印象,在诗中能够跳出窠臼、写出新意很难。对拉萨,你提炼出“天堂来信”这个核心意象,真是人人心中有却个个笔下无,到最后一句“背负不起的东西,不如放下”,卒章显其志,言有尽而意无穷,境界全出。对阿里,你以“遥远之外的遥远”来命意构思,为这片生命禁区平添了多少“宁静、祥和、清明、隽永”的诗意,赋予了哲学般的沉思色彩。《若尔盖大草原》中,你另辟蹊径,不急于写景,而是细细地写人,写人的生动细节,“有山必有好水,好水必有好人家”,泽巴满老人、易当措、万玛央金、程秀芬、次忠卓玛、扎尕、多吉卓玛……这是一个个好人家孕育出的好人,这些朴实而鲜活的好人才真正配得上若尔盖大草原的辽阔与纯净,而其中巧妙插入的自我行走和历史追忆,又使得全篇不至于成为简单的好人好事的絮叨,有了时空的纵深感。有的篇章写得迅疾而富有节奏感,如一些边塞短章;有的篇章如《伊犁河谷》则写得舒展、从容,如河水般流淌。《极边第一城》将一部沉硬的石头历史写成了灵动的心灵化的历史,赋予石头以温度和记忆。《大地》这样最容易写得大而无当、空泛无着的题材,你却巧妙地选择从故乡的水进入,“泾江水库的水,走了很远的路/蜿蜒曲折,没有捷径/长途跋涉走进大角卜村,已变得明显的消瘦/蹒跚中,脚步有些提不起劲”,这种不动声色、近乎白描的书写,实质是“近乡情更怯”的现代诗性版本,这样轻盈而深情的进入,就为“大地”这个宏大的主题打上了极其温馨、亲切的生命底色。
其四,是对城市诗写作的有力开拓,这一点尤具启示意义。
在《黄河长调》中,《上海谣》是一首别调,风格与其他边疆题材迥异,显示出你宽阔的驾驭能力。你在诗中写道:“于是,大上海的人被环境塑造得/极其传统、极其世俗、极其自我/却又极其前卫、极其精致、极其包容”,这六“极其”何尝不是你想塑造和表达的上海城市精神内核?从深邃的历史沧桑写到当下“真切的生活场景和日常味道”,这纵横交错的笔法构成了诗篇的经纬,这为现代诗歌如何书写城市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标本、一种崭新的可能、一份宝贵的借鉴。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观察,就是,我们的新诗,对城市题材的处理整体上是有缺陷和不足的,至今没有出现像惠特曼歌唱纽约、桑德堡描绘芝加哥那样的书写中国城市的大手笔、大诗篇,实在是太遗憾了。其中原因,与我们这个古老文明深深植根于农耕社会的文化传统有关,诗歌中可借鉴的城市意象资源确实有限,即便像唐宋诗词中那些描写长安、汴京、苏州、杭州的城市题材作品,也大多被其田园山水光芒所遮蔽,没能引起后来者足够的重视;像汉赋中《两都赋》《二京赋》那样的城市赋,表面流光溢彩,极尽铺排,但现在看来,也多停留在物象罗列,缺乏深层心灵观照,没有多少可资现代诗歌借鉴的真正营养。现当代也有部分以城市为题材的篇什,但大多零散,不成系统,未成气候。记得那年在湖南,偶然见到唐晓渡先生,闲聊中无意中谈起这个话题,他不无遗憾地说到大诗人艾青,说他写巴黎、马赛等异域都市风情写得真好,深刻而现代,可惜的是回国后没有多写写中国的城市,特别是现代转型中的城市(大意如此)。
我本人出生在农村,二十来岁才第一次真正接触和进入城市,如今在城市中生活已四十多年了,但精神根基和情感记忆往往不自觉地回到乡村,城市说来说去还属于客居之地、谋生之所,这就打上了先天的印记,始终不敢对城市轻易说三道四,即便偶尔写几句,也会时不时露出“乡村”的狐狸尾巴来。自知先天不足,后天难补,奈何!而你不同,你曾经深入写过深圳,对现代城市有深切的体验和长期的观察,不妨今后多写。城市题材确实不好处理,容易流于表面化或概念化。然而,路总要有人走出来。相信以你的笔力、视野和行走经验,一定会继续在这条路上探索下去。我对此抱有极大的期待!
拉拉杂杂、信笔由缰地写了这许多,大都属于阅读后的即兴想头和零星感悟,逻辑未必周延,思考未必深入,仅供你参考和批判。对诗歌史上有些问题的个人说法不一定准确,我姑妄言之,你就姑妄听之罢。惟愿没有误解你的诗心。就此打住!顺颂秋安!
梁粱
2025年9月2日


梁粱,1955年生于山西省岚县,1979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曾任某杂志主编。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有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出版诗集、散文集、纪实作品等十多部。作品入选全国性多种选本,曾获多种文学奖项。诗集《远山沉寂》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


李立,著名环球旅行家,环中国大陆边境线自驾行吟第一人,足迹遍及7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文学批评家喻为“中国当代最经典的行吟诗人”“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第一行吟诗人”。作品见于《诗刊》《人民文学》《花城》《创世纪》等100多种主流报刊,获博鳌国际诗歌奖、杨万里诗歌奖和悉尼国际诗歌奖等十数次。《中国行吟诗歌精选》年度选本和《中国行吟诗人文库》诗丛主编。出版诗集、散文随笔集和报告文学集共7部和英文诗集1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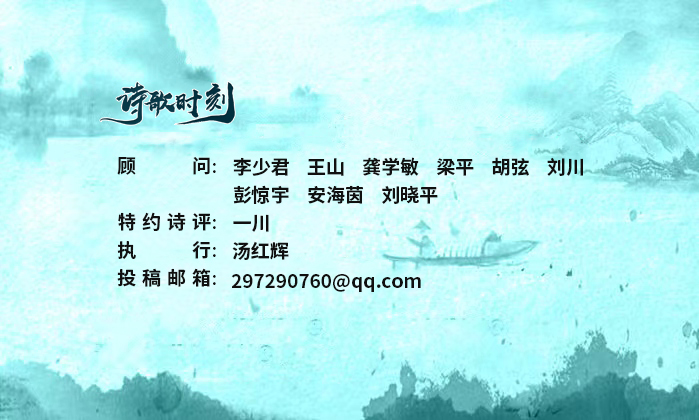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梁粱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化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