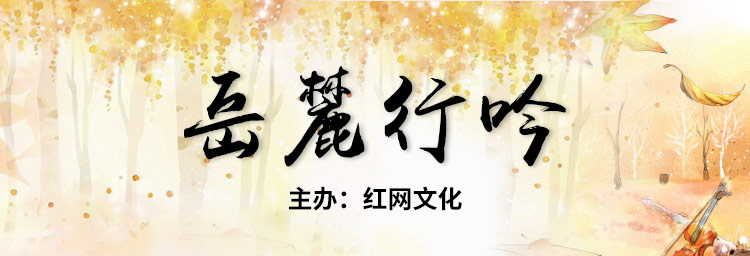

我和宁师有个约
文/刘凯希
我与宁师的约会,美丽幸福,却又充满艰辛。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上学的孩子特多,乡乡都办中学、村村都办小学。因为老师少了,一部分本已扎根泥土的高中生“洗脚上岸”,到学校当上了民办老师。这种临时应点“凑拢班”,没受过专业训练,各方面自然会有差距。所以,后来就有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系列政策措施,其中有一条,就是择优招录到师范学习,再按期转正。我就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
我们读书的学校在宁乡县城,叫宁乡师范,习惯称“宁师”,一所很有名气的老牌师范学校。当年,李维汉曾在这里主持成立中共宁乡第一个支部,代号“宁觉”。徐特立、谢觉哉两位老前辈都曾在这里任教。
印象中,宁师校门朝南,有个简单的牌楼,上方有谢老题写的校名,黑色底板上,金色繁体字苍劲有力,很有厚重感。出门左边是宁乡实验小学,右边是宁乡公安局。门前一条小溪蜿蜒,曰“化龙溪”,曾是居民洗漱的地方,因为后来搞旱厕改造,溪水便变得有些脏臭,被戏称为“化脓溪”。溪上有两座便桥,一座通往学校食堂和教工宿舍,另一座则通往一条窄巷,叫“火宫巷”,巷口挂的那个“康益旅社”的牌子还有些印象。
校园内也比较简单。进门左边两栋砖木结构的老式房子,楼上铺的木板,是“民师班”宿舍。右边也有几栋,前面是教学楼,后面则是“普师班”宿舍。中间一条通道,正对着几十级青石台阶。教学楼前面有块空地,周边古木参天,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冠,洒下斑驳的光影,写满诗意。同学们往返学校,都喜欢在这里放下行李歇脚。还有个大礼堂,一栋职工宿舍。右边位置最高的地方有个土操场,用围墙围着,每天一早,我们都在这里出操。
普师班学生占大多数,都是从初中毕业生里面挑的,十六七岁,充满朝气。那时候,能考得上师范的初中生都很“牛皮”,基本是乡村中学里的“学霸”,走到哪都有人竖大拇指。别看只是个中师,其含金量可不低,三年毕业,直接分配到当地小学任教,稳稳当当的“铁饭碗”。民师班就我们这批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人数并不多。我们的学制是两年,脱产读书只一年,另一年回乡镇实习。记得我们这一届是先读书后实习,上一届则是先实习后读书,两届加起来,也就八个班,不到400号人。
和普师班的学生不同,我们多数都有家有室,或是家庭主男或是家庭主妇,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把家庭割舍的。于是,平衡好学业与家事就成了我们的“必修课”。学校也充分考虑实际,在作息安排上给了很多“优待”。那时没有双休,通常,我们都是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我老家在宁乡、益阳、桃江交界的地方,离县城约50公里,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往返学校的路上,唯一靠谱的交通工具就是“桃江班”,来回桃江长沙的大班车,从老家那边到县城,好像要七八毛钱车费。
回家那天,大家都很兴奋,很早就开始准备。除了清点换洗的衣服,少不了要用节省下来的饭票,到食堂买几个馒头。宁师的馒头个儿大、味道好,乡里一般吃不到,带上几个给家人或邻居分享,绝对是“口福”。放学了,大伙就火急火燎地赶班车。从学校到宁乡汽车站有段距离,一般就走路。实在来不及的时候,也得叫个“叭叭车”,三轮摩托改装的,加了个油布篷,里面能坐两三号人,不过要花一两块钱,心里总有些舍不得。
“桃江班”是过路车,班次相对固定,而且很少进站,所以只能站在路边等。远远地看到车来了,就迫不及待地往上挤。车上早已挤得爆棚,有座位的似乎并不在乎,悠闲地打着瞌睡;没座位的一个劲地往人缝里挤,希望找个东西扶。售票的则不停地忙乎,从车头挤到车尾,一个劲儿嚷着“买票”,然后一个一个地收钱,在铁皮盒子里扯上车票给了,才算基本安定。要是有急刹车或急拐弯,站着的人群就会“一边倒”,跌跌撞撞是必然的。这可是“扒手”下手的最好时机,一不小心把袋子里仅有的几块钱弄丢,回去就不好“交差”。因为平时坐车少,我一上车就不舒服,顺顺当当走倒没什么事,若是停车上下客,“嗤”的一声,那种汽油味便扑面而来,肚子里立刻翻江倒海,够难受的。好不容易熬到熟悉的路口,就要司机“踩一脚”,赶紧下车走路。本就疲惫不堪,加上肩上背的、手里提的,走两三公里路,要个把小时。有时运气好,也能搭上个“手扶拖”之类的顺风车。
回到家里,已是傍晚时分。妻子早已准备好饭菜,一边端茶倒水,一边问这问那,很是亲热。儿子还小,但识得了人,拍打着要我抱,恋在怀里不肯放手。两口子一起看看电视,商量好第二天的活,便哄着儿子早早休息。第二天就按计划行事,挖土、种菜,踩草、施肥,安排得满满当当。下午忙完,洗个澡、带上衣物,又匆匆赶路。若是赶不上车,周一早上天没亮就要出门,不然会要迟到。
我所在的是民师904班,四十几个人,都是宁乡、望城来的。大伙都很好相处,而且各有特色。有几个喜欢说笑的“策神”,有几个讲起“升级”就来劲的“老顽童”,也有几个讲究搞点写写画画的,还有独自坐在角落拉扯二胡自娱自乐的。
在宁师读书,我们的文化课其实都是“炒现饭”,因为我们多数都已高中毕业,有的还搞过中师函授,学的大体差不多。关键还是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我们的课程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块。《算术基础理论》是左玉辉老师教的,印象最深的是她归纳的“顺口溜”,精辟精要,很有技巧,比如教“多位数零的读法”,就有“0的读法要记清,级尾有0不发音,级头级中0都读,连续几个读一声”几句,让人过目不忘。曹建伟老师教的《教育家教育思想》,表面有些枯燥,细品却意味深长,诸如孔子的“有教无类”、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夸美纽斯的“班级授课制”,对我们后来的教学实践都很有影响。宋光武老师教书法课很有一套,一边讲“点如瓜子撇如刀”之类,一边拿个湿抹布在玻璃黑板上写画,用粉笔沿着印迹边沿勾勒一下,方方正正、秀美有力的汉字立刻呈现出来,令人叹为观止。教美术的是戴虎强老师,年纪和我们相当,个子不高,虎头虎脑,留个长发,蓄点小胡子,一个典型的“艺术青年”形象。因为还没成家,很多时候就和我们几个喜欢画画的“混”在一起,成为了“铁杆”。教普通话的胡茂林老师也很年轻,人美音甜,听她讲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但凡教过我们的,在我心目中都是值得敬仰的师长。
老师教得好,学生自然不赖。在民师班里,我算是学得比较用功的,每次考试成绩都不错,即使是五音不全,乐理考试也打过98分,就连从未摸的风琴也能勉强弹上几曲。记得有一次,学校还安排几个同学帮我,到隔壁的实验小学上了一堂“思品”研究课,且不说上课好坏,单就乡里老师到城里上课,这个机会就很难得。
课余,我们玩得多的就是“升级”。宿舍里,我们都有一把集会坐的蓝色小木凳,一块上美术课用的小画板。只等放学,几个爱玩的就“嘭嘭”上楼,搬上凳子、搭起画板架场,多的时候有两三桌。尽管是闹着玩,但大伙都很认真,为了争个输赢,有时甚至饭铃响了还舍不得散。也有三两成群逛街的。顺着火宫巷往南走百把米,向右拐个弯,便是宁乡北正街。工人文化宫、宁乡工农饭店、宁乡百货商店、宁乡花鼓剧院和宁乡县政府等地标性建筑,都集中在这一块,很热闹。我常去的却是南司湾,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巷子,传说这里曾有“八条好汉”,都是大人用来吓唬小孩的“神器”。最喜欢这里的瓷器,锅碗瓢盆样样有、价格也便宜,随便挑几个回家,妻子一定很高兴。偶尔也会“洋气”一回,去文化宫前坪吃吃宵夜,这里摊位很多,灯火通明,臭干子、烤鸡翅、嗦螺、炒粉,应有尽有,大家围坐一起,不分彼此,相互请客,吃得津津有味。
一晃就是一年,该回老家实习了,大家都有些不舍。说是实习,其实与正常上班没啥两样,只是偶尔跟学校有些联系。我实习的地方不再是原来的村小,而是换到了乡里的中心小学。这是一所全新的学校,乡里村里都很重视,安排的多数都是刚从师范出来的年轻老师,很有活力。期间,民师总支的老书记还亲自来看我,了解我的情况,一再嘱托乡联校的领导要“好好培养”我,让我很受感动,很受鼓舞。
在宁师,虽然只短短两年,但我所付出的、所获得的却是空前的。我后来的每一次工作调整、每一次成长进步,都得益于那两年的潜心修炼。
毕业以后,大家都很少回学校。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我一年还能去上一两次,偶尔也碰上过熟悉的老师。同学之间也少有联系,直到近几年,班长和几个热心的同学才建起了同学群,搞过几回聚会。阔别重逢,同学们的喜悦如同烟花在心里绽放,脸上露出沧桑的笑容,大家相互问起各自的境况,回忆起在宁师读书的点点滴滴,很是感慨。
如今,宁师不再是以前的宁师。几经调整搬迁,宁师已升格为长沙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址也重新回到了曾经热恋的宁乡故土。同学们不再有当年的豪情锐气,多数都已告老还乡,在家里当起了“研究孙”,有几个还悄然离去了。
但不管怎样,宁师在推动长沙基础教育发展这一块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曾经作为全市“小学教师培养摇篮”的地位永远不可撼动。在这里学习进修的一代民师,用“粉笔+黑板”这种朴素的方式,坚守乡村学校半辈子,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撒在乡村课堂里,为孩子们撑起了一片幸福蓝天,历史永远不会忘记!

刘凯希,小学教师出身,多年在省、市、县教育行政部门从事政策研究、文字综合和教育管理工作。曾发表多篇文学作品,出版多部专著。现供职于长沙市某机关。
来源:红网
作者:刘凯希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化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