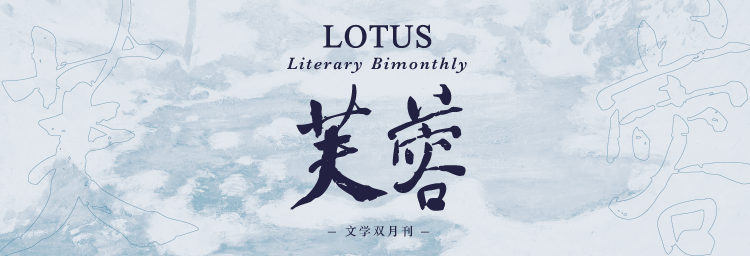

植物记
文/胡启明
榕树
我喜欢树,尤其古树。比方西北的轩辕柏、黄山的迎客松、彩云之南的大榕树等。我一直深信不疑,能和古树相见者,那必是有缘之人。不然,那活了上千年的古树,你凭什么说见就能见呢?每次和古树对视,总感觉这是上天对我的恩宠,是莫大的幸运与荣耀,心底就生出无限的敬畏。
我生长在穷乡僻壤,那里仅有浅山瘦水,小树小草、禾苗、棉花、小麦、大豆之类的植物,哪曾亲近过万花如绣的园林?更不晓得世上还有千年以上的树祖。
在“植物王国”云南,有个读起来极拗口的七弯八拐的地名,叫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铜壁关老刀弄寨,旁边有一棵了不得的大榕树,人称“榕树王”。从斑驳陈旧的碑石文字介绍看,委实来头不小。其树身奇大无比,当地傣族朋友很神气地说:“我们曾试过,几十人都合抱不下这棵树呢。”待我细看,但见其主干上布满了块状根系,如同山脉、峡谷,千沟万壑,大榕树上抛出一束束粗壮的气根,恰似一条条巨蟒把头深深扎进泥土中,看它那横行霸道的架势,像是要将地下的水全吸干一样,仿佛在这个地球上唯它独尊。整棵树枝连枝,根连根,构成一道“独树成林”的奇观。这大榕树不愧是热带雨林中的一绝,人称亚洲“榕树王”。这可不是乱封的,经植物学家测算和考证,盈江大榕树覆盖面竟达5.5亩地,其气根入土后长成的新树干就有108根之多。这可以看作是它的子子孙孙,它老人家至今已活了千多岁呢。它是中国最大的一棵古树,游人至此,无不惊呼,更有古老的传说为它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相传大榕树以前并不出名,地方上一些刁民对它还大为不敬,蓄意破坏它。哪晓得这些人后来不是家庭不顺,就是得怪病一命呜呼。这时,人们才猛然意识到,它是一棵神树,再不能伤害它。从此,当地人把这棵大榕树当神一样供奉着。说也奇,这地方上下之后果然是风调雨顺、人寿福康了呢。
我虔诚地站在大榕树的不远处,在它脚下我不过就是一小小的蝼蚁。我久久地对视着古树,思绪忽然一下穿越到1000多年以前。太阳和鲜花对话,月亮和河流对话。我也可以和眼前的树王对话。大榕树哇,不知是当年谁栽种了你,还是你这颗种子随风刮来,在此生根发芽并永久爱恋这片大地呢?在这十多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你从一粒种子到今日雄霸一方,也不知见证了多少人世沧桑,经受了多少狂风暴雨电闪雷劈,加上不懂事的人类和野兽的破坏,而你却恒久与之抗争,终于强大挺拔,且养育出一代代优秀的子子孙孙,构建了一个大到无与伦比的“榕树家族”。你完全有资格称得上“德高望重”,是树祖的树祖了……
一阵山风轻轻拂过,榕树那遮天盖地的树叶沙沙地活跃起来,像是在微笑,像是在频频点头,又像是在慢声细语诉说过往的岁月。植物是有语言的,我估摸这树王也当是有一肚子故事的。临别,我走近大榕树,将脸颊贴在它的身躯上,我无意去沾享它的福寿,然我此刻的心跳、呼吸似乎已与它的生命紧紧地融在一块。看久了,我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自己仿佛也变成了一棵树。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原本对古榕树王的顶礼膜拜,很快就发生了一些微妙改变,那是因为榕树还有另一面不为人知的性格。诚然,这样的改变,也还不至于影响到我对它的尊重。这是发生在我从德宏抵达西双版纳后的事,我发现植物界居然也有残忍的“家暴”。同是植物家族,却用上了如此要命的手段。
这是我不敢想,也不愿见到的一幕。
两棵二十几米高的榕树和油棕树,居然绞到了一块。
那长在里面的是深棕色的油棕,头顶无可奈何地长出些不黄不青的叶片来,像个明显营养不良的孩子。长在外面的榕树呈深灰色调,霸气十足地将油棕从下而上死死缠绕个严实。
于是,这榕树便有了“亚热带雨林第一号杀手”的称呼。
真想不到,这大自然居然也不平静,有厮杀,也有笑声和哭泣。这虽然是树,但不也分明表现出一种生吞活剥的残暴吗?此刻,我留神察看,只见那油棕树上隐隐约约有黑色疤痕,我想这一定是它常年流下的泪水所致吧。
我拨开榕树张牙舞爪的枝丫,轻轻摸了摸里面那棵油棕树的干,我真怕触痛了它呢,因它的心灵早已伤痕累累,而它脚下这片深情的红土地的养分似乎都给了榕树。它的生命苍老了,不幸的命运注定它永远逃不脱这恶家伙的纠缠。
油棕也和所有的植物一样,它的各个器官,是由不同的细胞组成的,相比动物,多有叶绿素和细胞壁等,可油棕的每个细胞也都需要营养供给和代谢呀,这样它才能和人一样正常生长。可如今它所有的营养都无奈给了榕树,你说,这油棕还有活路吗?
导游说:“是风刮来的榕树种子飘落到了油棕树的周边,生根长大后慢慢就形成了‘榕绞杀’啦,这棵油棕要被榕树绞杀70年才能绞死呢。”“那么已经绞杀了多少年呢?”我不安地问道。“据植物研究所的人说,大概已绞杀40年了吧。呵呵,快了快了,你看嘛,这不是已经绞到油棕树的腰部了吗?”导游说到这时脸蛋上两只小酒窝一软,又飞出一个迷人的笑,她似乎一点也不心疼油棕。
哦,可怜的油棕树,倘若这样推算,你岂不是还要忍受30年的残酷绞杀才可以终结自己的生命吗?你没有生命的自由,你甚至也没有选择死亡时间的自由哇!在这最美丽的森林公园里,所有的阳光雨露也似乎全被榕树霸占了,你的生命还不及一只小小的蝴蝶受到珍爱,你终生的不幸与痛苦又能向谁倾诉呢?谁也不能救你,你也不能救自己。
油棕树啊,油棕树。
我心中积了一层莫名的惆怅。我是多么同情它的不幸遭遇,我虽没留下它的倩影,它却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清晰的印象。我掰着指头算了算自己的年龄,又掰着指头算了算油棕树的宝贵生命。哦,还有30年吧,那油棕树就不复存在了。也只有等到那时它才真正获得了自由呢!我呀,也或许不在了。
油棕不在,我也不在,榕树还在。
胡杨
认得胡杨树,最初是在宁夏镇北堡西部影城基地。按我以前的印象,此物应是在新疆生存,不知何时银川也有了它的踪影。眼前几棵光溜溜粗大的树桩埋在沙丘里,且见明显的锯枝痕迹,我便怀疑是从远方移植而来,是追水而来。因它身边就有黄河与碧清的沙湖。我很奇怪这树怎么会没有皮呢?这样裸露的生命是无论如何也经受不住凶顽的西北风撕扯的。树上钉有一块小牌牌,大概就是胡杨的宣言: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后来,我才又很傻地知道,面前的胡杨已经活过一千年了,现在是到了“死而不倒一千年”的阶段。那么在它整个漫长的生命过程中,还该有最后一个“一千年”。胡杨原本也有美丽的“衣裳”,只是它自动脱离了肉体。
这就是胡杨三千年的守望。
胡杨死了。不过,它的灵魂还在,夕阳下千奇百怪,形态各异,有苍凉而孤寂的美。
从银川回到南方,不知为什么,我对胡杨树的印象总是挥之不去。
不久,我终于又有一次难得的机遇,走进了胡杨真正的故乡——新疆塔里木。
秋日的胡杨林真是浓烈的浪漫与壮美,放眼望去,仿佛走进了一个金色世界,这与在银川见到胡杨已然大为不同。让我大感惊喜的是,记忆里那里的胡杨已只剩下骨架与灵魂,而眼前的胡杨却仍唯美屹立,美如画卷。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像无数金银闪烁,斑驳的光影在地面上不停地跳跃着,光是沉稳的,影却有些凌乱,仿佛诉说着它在大漠的前世今生。
许多人都说胡杨是“会流泪的树”,可又有谁能说得清胡杨为什么会流泪呢?更无人知道它深藏的生命密码。它终年总是流着泪,这完全不应是它的性格。然而,树竟和人一样,也有两重性。它一边日日为什么事悲伤,一边又雄势地活下去,并把宁死不屈的壮烈在天地间演绎得浩气长存,这当然会让人感到十分感动、震惊。可以说,胡杨的精神真是人类和大自然的一种骄傲。
胡杨生长在沙漠,人们对它还是多少有些误会。其实,它原本并非为荒漠而生,是为爱,为水而生。胡杨一生追逐着水的足迹,无论它走到哪里,胡杨都会跟随到哪里,就像一对生死都要在一起的恋人。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后来,因沙漠的变迁、河流的改道,最终,水忍痛将胡杨遗弃在一片大漠上,而它却被迫远嫁他方。
水离开了胡杨,绝望的胡杨把自己的根系疯狂地扎进更深的地下。它知道,以后的日子,只能靠自己了。胡杨必须用余下生命独自承受狂风沙暴的肆虐和折磨,需要在漫漫干渴难耐中,为曾经有水的滋润付出生命的代价,它认命啊。
胡杨当然晓得水的珍贵,因此格外珍惜,当遇到水的时候,它会让水把自己的身体储藏得满满的,在往后的日子里,它流出了泪水,这难道是它顽强活下来之后的喜极而泣?难道是它担忧前途而陷入深深忧虑的表现?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植物学家一说起胡杨,眼里就会充满盈盈泪水。
胡杨在维吾尔语中,被称为“托克拉克”,意为“最美丽的树”。它耗尽体内所有洪荒之力,释放生命的能量,绚烂了整个沙漠,惊艳了天地间。世间再无一棵树能够美过胡杨生长千年,傲立千年,不朽千年。它在等待着水的归来,等待着它迷恋的人归来。
自然界也有生生死死,似乎也遵循着某种规律,但它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终结,那只是完成了一次生命的轮回。然而,人类的强烈干预,会加快它真正灭绝的脚步。
胡杨虽死,灵魂却不朽。
胡杨啊,你以不可复制的姿态站立成永恒,站成了让人魂牵梦绕的神话,你孤傲地等候365天,难道就仅仅为着这短暂的绝美绚丽?
胡杨是荒漠的赞歌和英雄。
(节选自2025年第3期《芙蓉》胡启明的散文《植物记》)

胡启明,湖南平江人,现居长沙。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199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芙蓉》《大家》等刊发表报告文学、散文、小说计220万字,出版作品五部。
来源:《芙蓉》
作者:胡启明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