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禅宗精神、中国古典诗词和斯奈德其人其诗
——在首届“南岳中国诗歌节”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文/刘起伦
一、禅与中国古典诗歌
佛教在大唐东土兴盛之后,禅宗思想对诗的意境具有莫大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虽然禅为宗教,诗为文学,但两者有相似性。禅宗自谓教外别传,就因为灵山会中,如来拈花,迦叶微笑,即是传法。好的诗歌和禅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可言说,只可意会,点到为止。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论诗如论禅”,又说:“禅道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宋金时期,中国北方文学代表,文坛盟主元好问更是说出:“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以表现诗与禅之汇流与融合。所以说,自唐宋以来,禅宗对唐宋诗的影响,禅与诗水乳交融汇成中国文化内在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身兼名僧与诗人双重身份的唐代和尚寒山,出生官宦人家。屡试不第后出家,其生卒不详,据说活了一百多岁。《全唐诗》收录了寒山诗312首。他的诗被称为通俗易懂,算得上当时的白话诗。他不仅写禅诗、自然之诗,还写与自己和尚身份格格不入的世俗生活之诗,比如他露骨地写妓女的调情、写夫妻生活的缠绵悱恻,而且观察细腻、体会入微,不能不说是异乎寻常的现象(汤贵仁:《唐代僧人诗和唐代佛教世俗化》)。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应了另一位唐代名僧悟云说过的话:“任性消遥,随缘放旷,但尽凡情,别无圣解。”
当然,作为他同时代的不少文人,也有认为寒山的诗不够典雅,缺少文采的。当代研究中国文学的巨匠、翻译界的泰斗英国人霍克斯也在某种场合指出,寒山是“浪得虚名”(余国藩:《宗教与中国文学——论西游记的“玄道”》)。但寒山对自己的诗歌颇为自许,他用一首诗自我辩护: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时间是最公正的评判家。时间证明,寒山诗是中国古代诗一枝奇葩,长期流传于禅宗丛林,受到宋以后的诗人文士喜爱和追捧,近代以来更是风靡欧美和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寒山诗在日本一版再版,形成了一股“寒山诗热”,有很多学者对寒山的诗进行研究、注释及翻译。
20世纪50年代以后寒山诗歌在美国传播影响也很大,得益于诗人加里·斯奈德对寒山诗歌的积极翻译推介。他英译的寒山诗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是因为诗歌中传递的禅宗文化。由于自身的禅宗情结,他通过自我境界的提升,对自然的热爱,对内心的修炼和世界观等诸多方面再现中国的禅宗文化。斯奈德奈1965年出版了一部诗集取名《砌石与寒山诗》,这是他的主要成果之一。斯奈德还有些诗歌直接与禅扯上关系。比如《牧溪六柿图》《禅寺春夜》《禅寺秋晨》等等。
加里·斯奈德曾说:中国文化、文学对他的影响,在五六十年代是百分之八十。所以说,研讨斯奈德诗歌与中国精神,不如说,探讨禅学与中国古代诗歌对斯奈德其人其诗的影响更为确切。
众所周知,在中国禅宗发展史上,南岳怀让与青原行思是六祖慧能南禅体系的两大枝干,高僧辈出,群星璀璨。南岳成为后世五家七宗圣地宗源。所以,在南岳召开这样一个研讨会,应时应景,实在是选对了地方,足见会议主持者的匠心独具。这是题外话。
二、禅与中国古典诗歌对斯奈德诗歌创作的影响
庞德、艾略特、弗罗斯特、W·S·默温、勃莱、加里·斯奈德等,都是我喜欢的美国诗人。但说实话,除艾略特和弗罗斯特作品外,其他诗人的诗歌我此前读的不多。斯奈德的诗歌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是近些年的事,这与中国开始意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诗人们的目光开始凝视大自然不无关系。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学写新诗不久,在一种以书代刊刊名叫《国际诗坛》的出版物中,读到过斯奈德几首诗及其人物简介,便对他发生兴趣,关注了这位诗人。我在对他的有限阅读中获得了管中窥豹、尝鼎一脔的快乐。
加里·斯奈德是个坚持自己诗歌理想且很有趣的人。他出生于美国旧金山,1951年毕业于里德学院,获文学和人类学学位,接下来又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东方语言文学,参加垮掉派诗歌运动。斯奈德在加洲大学修中国教授陈世骧的中国古典诗歌课时,深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他在陈教授指导下翻译了二十四首寒山诗。寒山诗中所体现的远遁、栖身山野、狂放不羁的形象十分契合他本人的审美期待(罗坚:《自修禅阶段加里·斯奈德对禅宗文化的理解及运用》)。醉心于研习禅宗和中国古代诗歌的他,于1956--1968年东渡日本(其时,中美没有建交),甚至出家为僧三年。1984年,斯奈德和金斯伯格一道,作为美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终于圆了他亲临“中央王国”之梦。这个诗路里程完全体现在斯奈德一首四行短诗《诗是怎样来找我的》里:“它跌跌撞撞,绕过/夜里的巨大砾石,受了惊吓般/停脚在我篝火的范围以外/我去迎接它,在那光的边界上。(刘川译)”
斯奈德所言的诗就是深深打上禅宗和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烙印的“黑马”找到了自己的骑士(布罗茨基在《黑马》一诗有诗句:它在我们当中寻找骑士)。
因为参加这个研讨会,近几日,我也从网络上搜索读到更多的斯奈德诗歌中译。斯奈德诗所提倡的生活与诗歌理念就是中国的天人合一,按现今流行说法,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前文提及,斯奈德师从陈世骧教授研习中国古典诗歌,且沉迷其中,当然阅读和学习的不止寒山一家,有斯奈德诗句为证:“我又听见/在公元四世纪陆机的/《文赋》里——序言中说:/“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我的老师陈世骧/多年前就译出并讲授它”(《斧柄》)。陆机是魏晋人。那么,陈教授不可能不给学生讲授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鼻祖”的东晋诗人陶渊明。同理,斯奈德翻译推介寒山,他不可能不接触并喜爱对禅学颇有造诣、写出禅意趣味深厚、流传甚广的唐代王维、宋代苏东坡两位顶级大师的诗作。
王维诗属于田园派自然诗,内容取材于山水景色,风格淡雅恬静,质朴自然,充满了浓厚的禅趣。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鸟鸣涧》《辛夷坞》《终南别业》等名作。难怪明代诗人、评论家胡应麟评王维《鸟鸣涧》《辛夷坞》二诗时盛赞:“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此妙诠。”几乎将之与佛经佛典等量齐观了。斯奈德翻译推介了寒山,但我个人认为,他的好些短诗,与王维的诗更相贴近,有异曲同工之妙。苏东坡居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上承欧阳修志趣,下开宋诗发展机运,赋予宋诗新活力、新生命。他广为后人传颂称道的庐山三偈,三首七言诗就受惠于禅宗思想之力。
所以,我可以大胆断言,斯奈德认真研习禅宗和中国古典诗歌,是将其作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基石的。
三、对斯奈德几首诗歌的解读
斯奈德很多诗歌创作,从立意到取材,从文法到修辞,无不透露浓浓的“中国风味”。取材与立意,多涉及人与自然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轻松、活泼、恬静,一切听任自然,不加勉强,诗歌风格趋向冲淡,深得中国古典诗歌之神韵。
接下来,从凌空蹈虚、泛泛而论中出来,选三首斯奈德诗歌,做蜻蜓点水式的品评和解读。而解读之前,我耳畔突然响起日本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的话:“禅的方法是把生命保存为生命,而不用外科手术刀去触及它。”“比如一朵花,花并无意识于它自己,是我把它从无意识中唤醒。”所以解读中我尽量避免使用外科手术刀,而是唤醒。
《进山》
他爬到浪花飞溅的溪涧边上,
他沿着平板似的岩石向上走,
他把手指放到水里,
他转身走向隔在一边的水池,
把两只手放在水里,
把一只脚放在池里,
把几块石头扔在池里,
他用两手拍打水面,
他高叫,起身站立,
面对激流,面对高山,
举起双手,三次高喊。
(杨子 译)
这是一首白描诗、也是一首口语诗。读它时,一个率真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没有宣教、不做姿态,诗行平淡得像禅家口头禅:“且喝茶去。”所以,我在吟咏再三后得其诗意,而且不由自主想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自得、想到李白笔下敬亭山的孤独壮丽、还会想到王维的五言律诗《终南别业》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诗句。
《松树的树冠》
蓝色的夜
有霜雾,天空中
明月朗照。
松树的树冠
弯成霜一般蓝,淡淡地
没入天空,霜,星光。
靴子的吱嘎声。
兔的足迹,鹿的足迹
我们知道什么。
(杨子 译)
这是斯奈德比较著名的诗,也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语言洗练,对夜间山林场景的静态描写,富有玄学意境和东方审美的气质,诗里有强烈的画面感。相比较《进山》,这首给予读者更浓郁的诗意。国内也有诗人评论家对这首诗进行很好的解读。我在阅读理解它时,是与王维的诗和禅宗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我读诗的前六行,脑海里会同时叠加王维《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辛夷坞》“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等幽静的画面,读到七、八两行,又觉得类似于“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的动态描述。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的四、五行:“松树的树冠/弯成霜一般蓝,”这样的描绘就完全是主观性的,在我们们常识里,霜是白的。与其说,月光制造了如梦如幻的感觉,不如说诗人在自己的意识深处就认定这霜就是蓝色的。这与禅宗的偈言相类似。禅的很多偈语都反常合道。最著名的一首是偈颂七十二首中一首:步行骑水牛,空手把锄头,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超越了人们常识习见。反常而合道。我还特别喜欢这首诗的最后一行 “我们知道什么。”看似突兀,实见匠心。其味在不经意间。这也颇具禅的意味。我们知道些什么呢?如佛家所言:“言语道断,不可说,一说就错。”一切都在心中。
禅寺春夜
八年前的这个五月
晚上我们漫步在俄勒岗
一个花园的樱花树下。
那时我想要的一切
现在全忘了,除了你。
在这夜色中
在古都的花园中
我感到了幽灵的颤动
我记起你沁凉的胴体
在一件棉织的夏裙下裸露。
(刘川 译)
这是一首深刻的伤时之诗。
诗题中的禅寺,当是斯奈德在日本出家的相国寺。斯奈德这首诗里有个我们不能忽视的关键词“樱花树下”。日本是樱花之国。我查了百度,日本的樱花开放是在三月到四月(寒冷的北海道开到五月)。而五月的东京,樱花已经凋谢。看着樱花凋落如雨,或站在无花的树下,都是很容易引发人们伤感与怀旧的,何况诗人!是相国寺的樱花树触发了诗人的记忆燃点。八年前,诗人和情人漫步在俄勒冈的樱花树下,是何等的美妙。八年之后,斯人安在?今夕又是何夕?我心头突然冒出样板戏里一句台词:“八年了,别提它了!”这里没有丝毫的戏谑情分,而是和诗人痛在了一起。此刻,诗人在东半球的日本古都禅寺,触景生情,再次想起往昔,深刻体会到人生的无常,惘然之情就像夜色一样弥漫开来。是啊,在春天、在夜里、在禅寺,最是令人伤心、伤时、怀旧。斯奈德这首短诗除了让我联想到苏东坡《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明月夜,短松冈”的诗句,也想到我自己《芦淞听雨》一诗中写到的类似感受:“优怀者不可听雨。闲愁之外/是回不去的故乡。”
四、结语或关于自己近年诗歌创作
因为时代不同、国情不同、人生经历和职业不同,我不可能拥有加里·斯奈德相同的行为自由,但我追求灵魂自由。所以,我的诗歌创作理念和斯奈德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契合,也就是说,我近年的诗歌创作,根植于中国古典诗歌之中的,我的灵魂和血管流淌着中国文化与精神的“蓝墨水”。军旅职业生涯结束之后,我也过了为一首激越之诗里语感的加速度而怦然心动的年纪,内心越来越趋向平和。这几年,我花了点时间在研读禅学以及禅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在重温中国古典诗词。而这种研读,不由自主地渗透到我的诗歌创作。这种影响也贯穿和反映到今年五月百花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版的诗集《月光正照着沉默的诗人》(中国行吟诗人文库·第一辑的一种)一书。正因为如此,在故乡衡阳举办的首届南岳中国诗歌节《斯奈德诗歌与中国精神》主题研讨会上,我不揣浅陋,做这个简短发言,就教于各位诗人和评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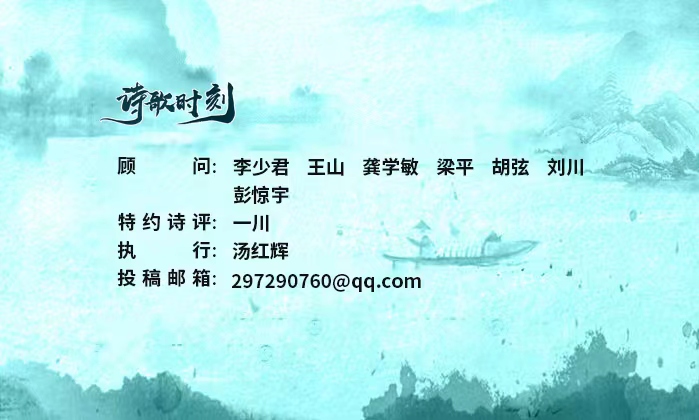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刘起伦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化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