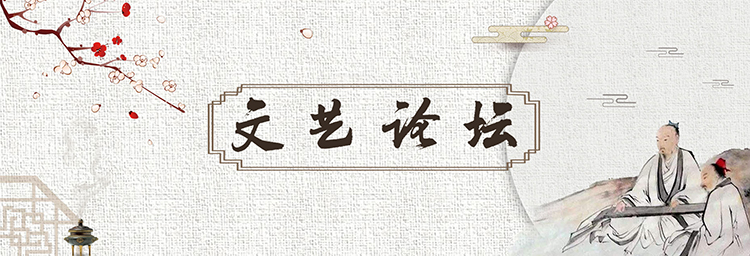

互动电影叙事艺术与价值探析
文/龚骁
摘 要:在数字化时代,电影和游戏之间的交叉和借鉴趋于频繁。互动电影的诞生不仅为导演叙事表达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观众体验电影赋予了新的方式。本文首先梳理了互动电影的非线性叙事特征及剧情质量的重要性,再对互动电影从公共场所转向私人空间的必要性进行了些许阐释,并认为互动电影其核心交互从“集体决断”向“自我对话”是符合影视市场与观众需求的。最后探讨的是“自我对话”的交互选择应该是深刻的,是可以伴随电影技术发展的,也是赋予互动电影更多意义和价值的。
关键词:互动电影;非线性叙事;集体决断;自我对话
电影与游戏(本文中特指电子游戏)在数字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存有不少的交集。除共享IP、共同延续外,游戏在画面制作上一直力求电影级画面质感所营造的临场沉浸,而电影编剧也渴望尝试电影能像游戏一样与玩家(观众)产生更多共情交互。互动电影,可以看作是“影游融合”的一种创新型艺术呈现,它与传统电影的线性叙事有所不同,其游戏化的非线性叙事路径可以“迫使”观众在观影中趋于主动。这不仅可以丰富观众体验,还可以为导演艺术表达提供新思路。在20世纪,因观影空间与技术支持的限制,互动电影的早期尝试并没有收获较好的市场效果。但在历史的今天,私人观影空间兴起,数字技术发展和大众已习以为常的游戏方式,互动电影的市场红利逐渐显现。如何使互动电影中的交互是顺畅和观众是乐于进行交互的?如何让影片中的剧情选择对观众而言是意义深刻的?又如何让前沿技术能够有效应用在互动电影中?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一、互动电影,一种影游融合的非线性叙事
电影与游戏的叙事都发生在人类所创造的虚拟世界,但相比游戏而言,电影的故事剧情一般会与真实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而在叙事形式上,传统电影以线性轨迹发展,故事的每一段剧情都需要导演编排妥当,观众则处于一种静态接受的状态。我们通过日常实践中形成的生活习惯也是去看电影,“看”侧重于视觉上的接触,观众看电影时多是以一种被动的,从视觉上反馈让大脑去接受的,无论导演如何设定剧情走向,观众只需静待它的发生即可。当然,也会有许多的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产生思考,思考固然是主动的,但即使是一千个观众眼中可以塑造出一千个截然不同的哈姆雷特,也无法改变客观发生的电影剧情和结局。这种精神上产生的共情效果和主动思考仅停留于观众自我思考的意识,而这种共情和思考所带来的深刻感则源自观众自身经历的催化。在游戏中,故事的发展一般都是以非线性进行的,游戏世界虽然也会存在边界,但体验游戏故事的发展过程却是可以受玩家控制的。所以,日常生活中,人们搭配游戏的动词一般会采用“玩”。玩是全身心投入的一种主动行为,交互体验会比看强烈得多(如自己玩游戏和看别人玩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玩家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游戏世界进行改造或观光。亨利·詹金斯将游戏叙事划分为“预设”和“涌现”。角色扮演类游戏(Role Playing Game,RPG),如大宇资讯公司出品的《仙剑奇侠传》(Chinese Paladin: Sword and Fairy)系列和《轩辕剑》(XuanYuan Sword)系列,就是标准类型的预设游戏叙事。玩家每一段自主体验游戏的过程最终会走向或推动剧情的发展节点(遭遇)和结局,且节点和结局都是已经设置好的。即时战略类游戏(Real Time Strategy Game,RTS),如暴雪娱乐公司研发的《星际争霸》(Star Craft)系列和《魔兽争霸》(War Craft)系列,则是一种涌现性的游戏叙事,在游戏中的每一秒所发生的动作都可以由玩家执行和控制,只要未经探索,就无法洞悉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游戏互动所产生的节点(遭遇)和结局也都会受到玩家思想和操作的影响,且每一局新的游戏都会产生不同的体验。由此来看,互动电影中的交互叙事类型更偏向于前者,类似角色扮演类游戏中的预设性叙事,因为即使在电影中产生再多的分岔剧情,也都是之前由导演和编剧所设置好的,观众无法创造导演设置以外的影响剧情推进的节点(遭遇)或结局。另一方面,互动电影的分岔剧情虽然是预先设置好的,但它发展的条件却是需要观众主动触发。所以互动电影不能以传统电影的线性轨迹去推进,这一点和游戏更为相似,是非线性的。在探讨这个问题时,也会有人认为传统电影剧情中也会存在“非线性”叙事的情况,如反向、回放、交替、剪辑等。爱森斯坦(Sergei M. Eisenstein)和他的蒙太奇实践也是如此,他将视觉和叙事上看似不相关联的影像剪辑在一起,目的就是意图在影像的冲突中激发观众的认识升华,以理性思考“互动式”地填补画面与画面衔接间的空白。②这可能会成为激起观众内心思考的涟漪,但在影片放映的整个过程里,观众实际上仍是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因为他们并不需要作出伴随个人价值或情感的剧情选择。这些“非线性”的叙事方式和内容也不会影响剧情的继续推进,甚至在叙事的尽头电影的尾声中还会交织在一起,一同组成完整的故事。而在互动电影中的分岔剧情内容虽然是有限的,但它不是无限分岔、随机跳跃的,也不允许观众在叙事情境内随意漫游。③但是它非线性的轨迹却是存在的,是必须在观众选择后才能进行的,剧情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选择都会打破原有时空的连续性,而且这种打破是被赋予“绝对意志”的,若不作出选择,影片的剧情就无法继续。互动电影中的交互过程就是在预设性叙事的节点中伴随个人价值和情感的一种抉择,这也是体现互动电影的交互意义之所在。
作为影游结合的一种艺术表达,互动电影以其非线性叙事的形式为观众创造了“玩”与“看”相融的乐趣,但互动电影的操作方式又是极为简易和便捷的,无法像涌现叙事的游戏一样需要玩家去全情贯注地操作和思考,观众在互动电影的体验过程中还是会更倾向于去“看”。既然无法通过操作的方式去填充观众的体验感,又为了使互动电影中的“玩”不至于沦为食之无味的“鸡肋”,影片内容的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互动电影一般会具备3~5条的故事主路线和几十上百个交错的剧情节点,所以互动电影的总时长相比传统电影而言会长很多,这就在剧情的容量上提出了较高要求,这些不同线路的剧情不能够有多余的重复,因为即使是两条相似的剧情线都会让观众感到厌倦;其次,互动电影中节点和线路的分岔必然会导致结局的不同,这不仅在剧情架构的逻辑设计上要有极为巧妙的构思,还需要对这种迥异体验去充分考量观众对剧情节点选择和结局设置中的价值肯定;最后,关于互动电影角色的选任也会存在更多考究,由于大相径庭的价值路径设定,剧中演员对于同一角色的不同剧情路线发展、价值判断、性格演绎和人物搭配都会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二、“集体决断”与交互性的冲突
互动电影的鼻祖是捷克导演拉杜兹·辛西拉1967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世博会捷克馆公映的《电影自动机》(Kino-Automat,又名《一个男人和他的房子》)。④这不仅是技术更新让电影剧情发展的权利首次掌握在观众之手,还是对传统电影线性叙事的一次超前挑战,这部影片的公开上映被看作是开了互动电影的先河,但初出茅庐的尝试并没有取得很好的市场效果。最初,大多数的观众会对这种“奇特”的观影方式充满新鲜和好奇感,并愿意购票进行尝试。但他们并没有获得理想的观影体验,难以为这种类型的影片进行持续付费,这直接导致互动电影无法在市场上推广,大众对它的新鲜感一过便很快落下帷幕。那么,为何这种新的电影艺术表达方式在当时无法受到观众的青睐呢?在20世纪,大众观看电影一般都是处于公共场所的电影院或大型场馆。互动电影非线性的叙事构造虽然赋予了观众推进电影剧情的权利,却受限于在电影院等公共场合需要进行的“集体决断”,这让选择权利的落实无法达到顺畅的状态。“集体决断”的交互方式对于互动电影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打破观影沉浸和模糊真实意思表达两个方面。
其一,关于沉浸。电影作品的呈现是多维度的,包括声音、画面、故事内容和叙事方式等。在电影艺术发展的历史中,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2D到3D,单线到多线再到非线性叙事,无论是哪一个维度都没有停止过对电影呈现临场沉浸的追求。这也印证了在观影过程中,需要赋予观众沉浸式观影体验的重要性。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提出的沉浸(心流)理论认为,沉浸的产生需要有明确的目标,注意力的集中和可获得的及时性反馈三个条件。⑤影片《电影自动机》在播放的过程中,其新颖的分岔剧情构思和节点中的主动选择权对当时的观众产生观影目标和集中注意力是有所帮助的。但每到剧情选择节点都需要由主持人引导观众进行二选一,获得票数高的剧情会继续播放,这就需要等待所有观众都选择完毕之后。而作为在公共场合下的一种被平均化的权力,仅仅是二选一的剧情发展都难以让观众接受,那么为了提供多价值观的三选一、四选一,甚至五选一、六选一实在无法想象。“集体决断”对观众在交互选择的观影体验中无疑是产生了巨大的反向作用。因为基于观影群体之间的复杂性和观众个体之间的认同差异性,主持人无法催促每一个观众都能够快速地作出选择,更何况有的观众会认为这个选择对于他来说是意义重大的,甚至需要经过深思熟虑一番。所以对于已经作出选择的观众而言,能做的就只能是耐心等待,而等待其他观众选择的过程对他们的观影体验就造成了一种物质层面(影片的暂停)和心理层面(沉浸的打断)相结合的双重性质的“强制性中止”,这是一种对观众观影临场的剥离,会使得他们无法获得选择后的及时性反馈,自然也就影响到了沉浸体验的效果。
其二,在观影中的“集体决断”方式还会模糊部分观众个体的真实意思表达,这种模糊主要体现在形式和内容上。互动电影在早期的放映过程中其选择形式为少数服从多数,这对于部分观影群体而言本就是难以接受的。比如,《电影自动机》在全片中共设置了9个与观众互动的节点,虽然每个节点只存在两种选择,但每一次的选择如果都按着某一位观众的意愿进行的概率却并不高,并且同场观众的基数越大这种概率就会越低。在当时的放映过程中,是由主持人根据多数观众的选择进行影片下一步剧情的播放,少数观众的意愿肯定就无法实现了。而伴随着后续影片在剧情时长和节点选择上的增量,几乎每一位观众都有可能成为“少数”中的一员。再加上每场电影观众群体构成的偶然性,和他们作出选择的随机性,即使是某位观众反复购票重复观影,要想完整观看一整部电影的内容还是需要具备非凡的运气。所以对于绝大多数的观众而言,他们在进行剧情选择时的个体真实意思表达会被概率化的“多数选择”所覆盖;接下来是剧情选择内容上的被公开化,相比少数服从多数的选择形式而言,这是更难以被观众群体所接受的。互动电影为了让选择存在区别能够对剧情走向产生真正意义的影响,剧情节点上的选择往往是会伴随着较为强烈色彩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个人情感的,这种价值的意思表示很有可能是南辕北辙的。当然,迥异的价值选择会使得节点中剧情的临场感更为真实,也更符合多样化的人性。但从社会道德价值评价的层面上来看,如果选择包含了积极的、无私的、纯真的,自然就会设立其对立面带来的消极、私欲和腹黑,甚至还会衍生出中立的、麻木的、不置与否的等。这对于具有社会属性的观众群体来说,多数观影的人肯定更乐意在公共场合中去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反映思想的剧情选择更是如此。电影院也是公共的开放的,每个个体所作出的剧情选择极有可能会出现在他人的注视之下或不经意的余光之中,那么,在有时带有真实自我意愿的选择就会难以表露。不论是独自观影被陌生人所环绕还是与好友家人一起携程共赏,当要作出选择(按下按钮)之时,多少都会被自我所认同的公共道德约束一二,哪怕是选择的后果只会产生在虚拟的电影之中。所以,互动电影的播放若处于公共场所的电影院,其“集体决断”的方式与影片特征所带来的交互必然是冲突的,交互所带来的价值也是受到限制的。
三、“自我对话”中的探索与思考
互动电影在早期并没有取得成功,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归于沉寂。直到数字化时代的社会发展促进了观影空间和方式走向多样化,尤其是个人计算机和智能电视的兴起,为互动电影的活跃和崛起提供了私人领域的空间。2018年12月,奈飞平台(Netflix)推出了《黑镜》(Black Mirror)的圣诞特别篇——《潘达斯奈基》(Bandersnatch)。从观影反馈和获奖情况来看,这是一部让互动电影真正走上风口的作品,《潘达斯奈基》的一般叙事流程为90分钟左右,全剧情总长312分钟,包含了上百个会对结局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选择节点,共存在5个不同的主要结局。如此规模的一部互动电影如果放置于“集体决断”之下应该不会产生太好的体验效果,因为光是等待其他人选择剧情的时间就会让多数观众难以接受。在今天,对大众而言,强交互非线性的电子游戏已是司空见惯,加上交互引擎的完善已经能做到极其快速地反馈,互动电影的形式在用户(观众)的接受程度上有了较大提高。而另一方面,由于播放渠道进入私人空间,互动电影中的选择既不用等待他人,也不需要少数服从多数,更不需要顾忌公共场所中的道德约束,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公共空间转向私人空间,互动电影中的交互从“集体决断”的方式逐渐演变为一种“自我对话”。
首先,互动电影的游戏基因会激发观众在影片中探索的欲望,每一个选择都会伴随着一些疑问。选另一个分支的剧情路线究竟会发生什么?这么选择真的是正确的吗?这个人物是保留好还是舍弃好?当然观众在电影院观影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只是由于集体观影的模式无法立即进行回放,除非多次购票反复观看才可能实现对当时没有选择的路线进行补充。另外,这还会存在另外一个运气上的问题,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有可能会因为运气,即使是多次观看也无法实现对影片的全剧情满足。互动电影中的探索体验必然是倾向于私人空间的。影片《潘达斯奈基》中有许多不同的结局,走上不同的分岔道路就会抵达不同的结局,对内容的全部探索可能需要花费7~8小时的时间。因为这和一般的游戏迷宫不同,迷宫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递进结构,常伴随着严峻的任务与单一的出口(例如奥德赛如何逃出独眼巨人的山洞)。⑥而互动电影所展开的分岔剧情形式更像是《魔法门之英雄无敌3》(Heroes of Might and Magic III)游戏中被“战争迷雾”(war fog)所笼罩的一张地图,只有玩家探索过的地图才是可观测的,但若要获得所有资源或达成所有任务又必须将地图进行完全的探索。这也符合艾斯本·阿尔萨斯(Espen Aarseth)所提出的遍历理论(Ergodic),在非线性叙事进程中,选择能带来差异化的体验,通过探索所有内容去考究整体的意义。⑦在互动电影中,当每条剧情每个选择节点都存在它的意义时,观众每次又只能进行一个选择,遍历的实现(体验所有剧情)就必然是伴随着反复、持续、整体的探索。除观众探索欲望产生的内驱力外,在《潘达斯奈基》的故事中,也一直散发着刺激观众去探索的气息。该故事由游戏设计师史蒂夫编写游戏程序开始,各种情节和台词一直会表示:我们在控制史蒂夫作出选择的同时,也被另一种未知(或更高级)的存在所注视(或控制)着(如我们每个人都处在游戏之中。我在奈飞平台上注视着你)。就如卞之琳诗句表述的一样,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种暗示在一定程度上会让观众产生被注视的感觉,当暗示作用与未观看的剧情交织在一起,会更强烈地促使观众去打开更多的剧情直至全部探索完毕。遍历需求的存在同时也再一次强调了互动电影要保障每一个细节的内容质量的重要性。
其次,分岔剧情中的选择应该是被赋予更多价值的,因为当选择如果变得不为重要,就没有人会去在乎是否该认真地对待选择。在“集体决断”中,观众可能会受到公共道德的影响,对于许多包涵中立、负面价值的选择是不乐意于接受的。从这一点上来看,互动电影中的教育反思功能会被弱化,甚至丧失。而在“自我对话”中,影片中的选择是近乎无所顾忌的,也是最为真实的。在观众群体中,有人注重“遍历”的游戏体验,自然也会有人偏爱“唯一”的无悔抉择。以自我价值观作出选择并一以贯之抵达终点,如果各个选择的延续和结局如果不符合观众对于该路径叙事发展的价值认同,影片也难以达到好的互动效果。“遍历”所带来的体验是分散式的,不同剧情路径之间的反馈是存在比较的,但带有强烈自我价值的“唯一”式抉择,其比较的对象则是自我内心的价值取向或憧憬。这会更加考验影片在内容制作上的含金量,巧妙构思每一条剧情路径上的各选择节点的发展逻辑的同时还需要保障内容演绎上的丰富和美感。
2019年1月,《隐形守护者》(The Invisible Guardian)在蒸汽平台(steam)发布,影片的制作方将其命名为“互动影像作品”,和以往互动电影略有不同的地方在于《隐形守护者》创新性地运用了图像定格的手法,精挑细选出的瞬间画面能为观众带来留白想象的些许空间,但这并不影响其互动电影的本质。该作品改编自Fantasia创作的“谍战”题材的视觉小说《潜伏之赤途》,讲述爱国青年肖途在抗战年代潜伏敌后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故事。“谍战”现在已经成为影视作品中的重要题材,但近年来国内市场的盲目跟拍、粗制滥造,给“谍战”题材影视产业蒙上一层阴影。而《隐形守护者》的出现为“谍战”题材影视市场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为解读经典题材提供了新的路径。⑧整部影片共设置了三条主剧情路线(扶桑安魂曲线、美丽世界线和红色芳华线)和四个主要的结局(扶桑安魂曲、丧钟为谁而鸣、美丽世界和红色芳华)。故事背景放在中华民族英勇抗日的年代,三条叙事线隐喻了那个时期的不同信仰与理念,大量分支剧情节点强化了各条主线的价值特征,在非线性的叙事过程中,导演结合了战争与历史的真实性残酷性,采用了符号隐喻的表现手法,将一次次的交互渗透到了正义与邪恶、现实与荒诞、沉醉与自省等矛盾统一体之中。扶桑安魂曲线设置的剧情选择一直是出于非角色人物本心的,作为关键人物理应肩负起身上的责任,但这些选择却无疑是逃避。原以为可隐姓埋名忘掉一切的活下去,最终却伴随着战争被死亡所埋葬。美丽世界线的叙事带来的则是一种关乎信仰会“一步错,步步错”的煎熬生活。为了坚持自己之前的错误选择,在明知会一错再错的道路上最终越走越远,体验到一个违背本心、违背信念的选择很有可能会让活着比死亡更加痛苦的领悟。而贯穿红色芳华线的剧情节点是被多数观众所认同的“正剧线”,一次次艰难的潜伏任务伴随着对正义的执着与信仰的坚持,最终抵达无悔的胜利彼岸。但因为经历的一切也带来了角色在精神上的影响,所以获得胜利的喜悦掺杂着一些不确定的感触,最后的隐喻指向战争是没有赢家的,只能给人类和地球带来灾难。剧中所有的抉择给予观众的价值体会是迥异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有伴随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的坚定,也有受到金钱和人性诱惑的犹豫和徘徊,甚至还有舍弃信仰的背叛。这些被赋予价值的选择是极为深刻的,在增强影片角色渲染的同时,也在观众“自我对话”的选择中进行了一次行之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
其他传统艺术历经几个世纪、伴随社会文化生活的逐步积累而来不同,电影是近现代媒介技术迅速进步的产物,尤其体现出它“技术性”的一面,技术的更迭和升级始终是其发展的第一推动力。⑨《电影自动机》作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互动电影,是电影技术和叙事手法上的一次革新,这种非线性游戏化的叙事表达为电影发展开拓了一方新的天地,也拉近了导演与观众之间思想交流的距离。《黑镜:潘达斯奈基》上映后的火热,为互动电影交互方式从“集体决断”走向“自我对话”提供了借鉴范本,也让以往交互与沉浸之间的矛盾得到了有效缓解。而《隐形守护者》的大获成功,不仅是因为观众对“影像留白”手法的接受,更是因为影片制作方对每一个剧情线路和选择节点的认真编排和对真实世界中人性抉择的细致考究,精雕细琢的打磨让“自我对话”的抉择变得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思考价值。在未来,虚拟现实和全息成像等前沿技术势必会在互动电影中有所作为,技术的更新和迭代能为我们的观影体验带来更为震撼的沉浸效果,但关于营造体验中的“自我对话”是否深刻的思考更该是互动电影发展中的应有之义。
注释:
①Henry Jenkins. Game Design as Narrative Architecture. In Katie Salen & Eric Zimmerman. The Game Design Reader: A Rules of Play Antholog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6. pp.681-686.
②万永婷:《交互主体性之外的新媒体艺术审美探究》,《文艺论坛》2019年第2期。
③张书瑞、孙星宇:《 媒介间性视域下交互电影的审美之思——以〈黑镜:潘达斯奈基〉为中心的考察》,《电影新作》2021年第4期。
④施畅:《互动电影崛起:媒介脉络与游戏基因》,《当代电影》2020年第9期。
⑤[美]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著,张定绮译:《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
⑥施畅:《作为迷宫的互动叙事: 冒险故事、分岔情节及多重未来》,《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⑦Espen Aarseth. Cybertext: Perspectives on Ergodic Literatu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pp.1-2.
⑧杜仕勇、徐莉军:《 互动影像作品的传播特征——以〈隐形守护者〉为例》,《青年记者》2019年第29期。
⑨王若存、 华楠:《 VR 电影〈杀死大明星〉的影像艺术生成》,《 文艺论坛》2022年第3期。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游戏创新设计与文化传播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SJYB064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传媒学院电竞学院、坎特伯雷大学)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龚骁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